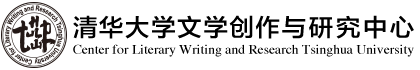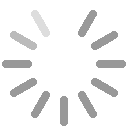消失的故里(2018文学奖二等奖)
2018.11.25
作者:姜伟峰,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信息学部,计算机技术专业。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在外求学,总遇到别人问起家乡,往往我第一句说一声“江苏”,第二句便得调侃地添上一句“不是江南”,这样,想要打开话匣子的问者,往往便都怅然若失似的,凝滞半秒,大家便尴尬地笑了起来。
江南着实太有名了,随处一瞥都是风物。比起“蛮夷”的江北,确是个风景人文俱佳的宝地。地理上的相近也让我有幸多次踏足这片土地,颇是羡煞。可我却着实不怎么喜欢江南的小格局,周庄太小,精致的苏州园林也小,连太湖都觉着小了些。所到之处,小城小屋,小河小桥,盛不住我的焦躁。
相比之下,我的家乡仿佛更合我心意。里下河是江北的一处洼地,水流纵横,倒也不枉水乡的称呼。放眼望去,水域广袤,浩荡的苇草、连绵的油菜花,颇有一番大格调。冯延巳写江南有“吹皱一池春水”的佳句,实在令人拍案叫绝。可泛舟于里下河的水面上,这水却从不是娇羞地等着风来吹皱,反倒是粼粼地生出一阵风来了,别有况味。春雪化泥,游凫戏水,新麦吐穗;夏躁蝉欢,梅黄杏肥,蛙鸣莲立;秋风拂稻香,冬雨竞寒潮。有了水,一切的生物仿佛就灵动起来,都在贪婪地吮吸着自然的恩赐。尤其是有了流动起来的水,连风也手舞足蹈起来了。
秋味:簖蟹别记
有水,自然就少不了水味。河鲜是生活在里下河的人们无与伦比的享受。以我而言,最爱的便是螃蟹。里下河的螃蟹自成品种,叫做“溱湖簖蟹”,与阳澄湖的大闸蟹有“南闸北簖”的合称。这倒不是蟹种的区别,而是捕蟹方法的不同而已。春暖之时,长江里的蟹苗洄游至内河安身,到了秋日,客居里下河的蟹便争相回江中产卵。
旧时渔人捕蟹,有两种方式,一曰索,二曰簖。秋日既要收稻,又要捕蟹,割下来的稻秆儿捆成一束,掺着稻芒儿,这便是索。把索浸在水里,将表层浸润一番后用火炙烧,在夜晚投于河水之中,索芯烘烤得暖暖的却不会燃尽,而秋日里河水渐凉,蟹便纷纷附在索上取暖,到了清晨,渔人抓着稻芒儿取出河中的索,便会收获颇多的蟹了。簖则是一种竹栅栏,与河面齐宽齐深,颇有阻隔河面之势。蟹实在是有攀爬的天赋,遇上阻拦,便自觉地沿着簖向着高处爬,出了水面,翻个个儿、便齐刷刷地掉进另一侧准备好的篾篓里,非得是强壮的蟹才有这能力爬上簖来,于是收获的也都便是膘肥的簖蟹了,自然也免去渔人遴选的麻烦。
簖蟹从中秋就可捕捞,持续两月之余,到入冬停止,而又以重阳前后的蟹最为丰腴。蟹可食用的部位多得很,其中又以蟹黄最为天上美味,这其中,母蟹的蟹黄则更受欢迎些。蟹黄的美味与否往往取决于颜色的鲜艳程度。蟹是最适合清蒸的,而要想吃到上佳的蟹黄,必须挑选强壮的活蟹现蒸现食。蒸成红壳儿的蟹里,红中泛金的母蟹蟹膏最是令食客惊艳。无需佐料,一整块嚼来,凝固的表层蟹膏里,蕴着的流质的蟹黄溅得满嘴留香,而细细咀嚼着固态的蟹膏,却又可品出另一种醇香而绵密的感觉——软软的蟹膏在舌尖瞬间缴械,仿佛化成一颗颗饱满的膏粒儿在齿间跳跃似的,酣畅淋漓得很。而公蟹的蟹膏则多以透明为标准,吃起来软嘟嘟的。除了蟹黄,蟹肉也是美味,蟹爪、蟹螯里的肉最为鲜嫩,颇为细腻温润。蟹肉之中,以公蟹的蟹螯肉最令人享受。蟹肉蟹黄多腥,配以伴有蒜泥姜蓉的醋亦可,可食客往往品的就是这种腥味,盖住味道反而有些浪费了。
最是品蟹时无所顾忌,想要完整地吃完一只蟹实在麻烦得很,因而此时顾不上双手的腥味,恣意地享受这美味才对得起自己。吃完蟹可以用茶洗手,颇有去腥的效果。在外读中学的时候,父亲知道我喜欢吃蟹,到了季节里总给我捎来;母亲也怕吃蟹耽误我时间,于是往往得花半个上午的时间给我挑出蟹黄蟹肉,蒸在饭里,或是做成蟹肉圆子、蟹肉包子,换我一刻的大快朵颐,真是难忘。
里下河的水里,并不单单只有蟹。螺蛳也是我喜欢得很的一道美食。红烧的螺蛳入味足,吸吮起来让人不能自持,很有嚼劲的螺肉汤汁饱满,也是酒席饭桌上少不了的佳肴。河蚌也常见地很,蚌肉鲜黄,用来炖豆腐汤颇受欢迎,可我却嫌太腥了些。银鱼是餐馆里少不了的炖鸡蛋或是炒鸡蛋的配料,蛋的柔滑与银鱼的鲜香的融为一体,增添了别样的口味。依水而居的鹅,也是家乡人交口称赞的美食,红烧的老鹅肉鲜嫩细腻,肉汁也很醇厚,总是家宴里的压轴美食。至于河虾、草鱼等等,已经是家常菜了。
水里养水味,也少不了清香的菱角和水芹菜。待荷花凋谢,就到了采菱角的时候了。采上来青嫩的菱角,煮透后变成肉色,咬开已经煮软的外壳,便是菱肉。用清水煮出来的菱肉,自有其本来的清香,平淡而回味无穷。
曾有幸在两年前的国庆假期回家,父亲自然少不了带我去买蟹。驱车的途中,路两旁却多了许多的池塘。印象里的这条路旁,往往是稻子长势最好的熟田。父亲得知了我的困惑,笑着说道:
“养蟹。”
我却顿时索然无味起来。里下河的渔人确实也已经越来越少了。旧时渔人的拿手好戏,就是用大网捕鱼,大网的四个角随着锚沉入河底,等上几个钟头,四个角同时用固定好的绳索一起拽起,渔网收缩,一网硬生生捕上来的渔获里,鱼虾满筐。靠人力起网得掐准时间,且耗时颇长,一般都得阻隔水道。撑橹摇桨的小船若是靠近了,往往船头的渔夫一眼就能看见远处有人起网,便将渔船停住,静静地等待起网结束。可现在,水道繁华,柴油船早就没有了乡里不成文的规矩,而捕鱼也无需这么繁琐,于是双方都又达成了新的默契了。外祖父家有个破旧的渔筒,喇叭状的网口让鱼虾易游进却难以游出,实在让我很是佩服这样朴素的智慧。
里下河也看不到清澈的水了。浑浊的水面让一条条河彻底地成了单纯的水道了。鱼塘倒是多了起来。将一片片稻田挖成鱼塘,是很多新的渔人的习惯。每年的三四月份,只需要从长江买来蟹苗,混着鱼苗虾苗,便都可以在一个鱼塘里等待着收获了。鱼塘密闭的空间里,打起激素来方便很多,于是丰腴的蟹开始在市场上多了起来,那包装盒上烫金的“溱湖簖蟹”四个潇洒劲挺的字、也都在笑盈盈地看着往来的顾客了。
死水,才不是里下河应有的水。
等到吃蟹的时候,不知是不是许久没吃、口味变得刁钻了,竟觉得差了几分味道、吃起来也多了几丝腥气来。
夏食:荷叶与糯米
复建的清芬园,在喧喧闹闹中开业了。窗口前人群攒聚,匆忙中瞥一眼菜牌,只看见“荷叶饭”三字,没有多虑便慌张而满足地排起队来。家乡虽不是江南、却也不枉称为水乡。水乡多苇草,荷叶也少不了。人民公园盛夏的湖畔里,满是无边无际的荷叶绿,点缀着的株株粉色的荷花仿佛也黯淡了许多。到了秋寒时,花已败得只剩下梗儿,油锅里的藕夹肉已经香的诱人的时候,塘中的荷叶虽枯、却依旧摇曳在风中。
荷叶多,便多了入菜的素材。荷叶饭也算是家乡一带的特色。如此,在清芬园里见到荷叶饭,说不上温暖亲切,倒也是值得一尝的。排了许久等到一份牛肉荷叶饭,轻轻拨开荷叶,细细品来其中饭菜,却也独得一份味道。牛肉里渗入一丝荷叶清醇的香气,饭也变得糯软了许多。筷尖划过荷叶,便可闻见袅袅的清香回荡,一如初晨露水滋润的明净的草香。荷叶粼粼,油在荷叶里也变得温顺得多。不知这荷叶是不是来自园子里的那一方荷塘,饭菜裹在荷叶里,仿佛处在一座烟雾缭绕中的庙宇,揉不进杂味,不消多时、便让这整个小小的世界紧紧地包裹在独到的纯澈之中。
荷叶饭让我小小地得意一番,也算是一次新鲜的尝试。家乡的荷叶饭主材决绝不是米饭,而多是糯米。棕色的糯米,杂着细腻的肉丁,铺上新鲜的排骨,更像是记忆里的美味。糯米本就是黏黏的,蒸在荷叶里,便更是糯糯。排骨也变得粉粉的,仿佛含在嘴里,无论是那骨还是附着的肉,便都化作齑粉钻进肠胃。酱油的浓郁与荷叶的渺远的香气,锤尽了肉的焦躁。于是,如此回味无穷的美食,便最惹得孩子们的欢喜。
糯米并不是罕见的食材。母亲用酱油泡上细长的糯米,蒸上一屉,白净的衣裳换作棕黑,没了娇气,变得糯软。这便是烧麦的馅儿。小时候最爱吃的早点便是烧麦,等到家里有糯米了,母亲也总是细致地蒸上一屉烧麦饭。每一粒糯米仿佛就可以嚼好久,黏在齿间,香味也是久久不散。糯米不易消化,母亲也经常让尚年幼的我吃得慢些、吃得少些,可这却只能直直地勾起我对糯米饭长久的挂念。
除了做成烧麦,端午时糯米也是主角儿。与端午一同到来的是弥散在空气里的粽叶香。母亲过了五一节就开始着手裹粽子——挑选新鲜的红豆、蜜枣与花生米,用从外婆家取来糯米和一些从池塘里新鲜割下的芦苇叶。家乡里称割芦苇叶为打柴草,芦苇叶上有两个似牙齿印一样的记号,老人们充满执念地将这与孟姜女联系起来——传说孟姜女哭倒长城后,变成一只鸟继续寻找着丈夫,飞到了里下河这片滩涂湿地,辨不清方向,于是便在柴叶上留下记号,防止迷路。芦苇叶选的自然是最为鲜嫩的,而用酱油卤好的鲜肉粒则很是入味,这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母亲就开始忙碌起裹粽子的事情来。
裹粽子第一讲究选材,第二讲究的便是裹法。最近几年离乡,吃的粽子大多是四角型的,这在家乡是不受待见的裹法,常常被称作草把式,两片叶子马马虎虎就能扎起来;最讨人喜欢的是菱角米式和小脚式,前者模样像是菱角,棱角分明,外形很漂亮,可是费粽叶;而母亲拿手的就是小脚式的粽子裹法,像只小脚太太的鞋子似的,可爱却不费叶子,往往三四片粽叶在妈妈手上、不需几下,一只粽子就有模有样了。锥形的底,配以侧面方方正正的顶,翻个个儿便像极了一只草绿色的绣鞋,小巧而精致。
素馅儿的粽子实在难以合我的兴趣,最让我欢喜的是肉馅儿粽。肉馅儿的粽子,除了在蜷成锥形的粽叶里盛上白色的糯米外,还需再放几粒红烧的肉丁儿,等到粽子蒸熟后,肉香渗进每一粒糯米粒中,整个肉粽儿就变成了浅棕色的糯糯的一团儿了。虽说黏,可每一粒却又明晰得很,一口咬下去粒粒都可品味。倒是买来的粽子,多了黏软、却少了粒粒的分明,拖沓而不干脆,实在是不合口味。大概,还是家的味道让让久久难以忘怀。
母亲每年都是要裹上好几次粽子的,分发给亲戚邻里。粽子从高压锅里捞出来的时候,粽叶清香瞬间飘满屋子,尤其是肉馅的粽子,轻轻剥开后,肉香的浓郁又混杂其中,实在诱人得很。小脚式的粽子粽叶厚实,因而比起四角型的粽子,往往使得糯米的黏与颗粒间的分明达到完美的平衡,糯软而又丝毫不拖沓,再加上鲜肉的美味,咸鲜而香甜的粽子实在让我停不下来。
在家门口扎上艾草和菖蒲,端午节就悄悄地来了。这一日,若是我在家里,是得吃“五红”的,汪曾祺先生在文章里说“十二红”,我倒是不曾见过。
不过,说起这端午的“红”来,必不可少的都是这咸鸭蛋。汪曾祺先生在其名篇《端午的鸭蛋》一文中写道:“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腌蛋’一条。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与有荣焉’。”
这大约是我对汪曾祺先生最不满意的一句话了——正是这一篇,竟“害得”家乡一带的咸鸭蛋都被高邮一地掩住了光芒——说起家乡的咸鸭蛋,倒并不比高邮的差几分,在这广袤且水网密布的里下河地区,麻鸭到处都是。春水涨了起来后,第一批鸭蛋用于炕坊里孵小鸭,得耐性子到了清明,鸭蛋才能用于腌制。腌制是个慢活儿,非得等上一阵子,才能吃到泛着红光、流着金油的鸭蛋黄。一般咸鸭蛋的空头在更圆的一侧,不过往往还得透着光找——敲开空头,一筷子直直杵进去,吱一声,油仿佛能咕嘟咕嘟地涌出来似的,一大块蛋黄塞进嘴里,饱满而粒粒分明,油而不腻,吃起来满足得很。到了初夏渐热的时辰,在家里吸溜着红豆粥,来个咸鸭蛋下粥吃,风扇呼呼地响着,真是抹不去的回忆。
除了鸭蛋黄,红萝卜、红苋菜、雄黄酒,自然也少不了烧红的河虾,这便是家乡的“端午五红”。可当这些突然涌现在脑海里的时候,我竟陷入一种渺远而漫无目的的思索之中。
夏日里家乡的美食实在是多得很。入夏除了鸭蛋,还有脆甜的西瓜。等到渐渐燥热起来后,外公家架上的丝瓜也熟了,清淡爽口的丝瓜汤总是能驱走夏日的闷热与烦躁。而到了菱角摆上日常餐桌后,也渐渐宣告了夏日的结束;直到莲子与莲藕上市,方才彻底告别了夏天。然而在外却自然讲究不起来。这么看来,竟突然觉得夏日悠长了许多。
春生:清明时节
坟茔和炊烟是村庄的象征。
进了村子,便随处可见坟茔。祖坟是万万不能孤零零地丢在田间地头的。于是,散落着的孤坟多是无名儿的,连块残碑也寻不见。雨水绵长,就像是暮色里渺远的炊烟轻悠悠地溶进天空里般,坍了一抔抔垒起来的土、又滋润起青苗来。
还在家的时候,清明节是得回去烧纸的。离乡的人春节可以不回来,可到了清明很多人离家再远也得回来一趟。进了村口,拐进爷爷家的小巷子前,必定是得在巷口提上几捆纸的。巷口有两家铺子,一家是个摇晃着赘肉的中年妇女,黢黑而红润的面庞随着她的笑扭动着,连眼角也蜷缩起来。另一家的铺子大些,是个精瘦的老年女人,白发也梳得整整齐齐,矮小的身材里蕴藏着不倦的能量。父亲多选择在第一家买纸。惨白或是亮黄色的纸用最简单的塑料片儿捆上两圈,打声招呼,好说话得很。临走时讨上一个打火机,那个中年妇人便笑着转身,用她只各剩下一截儿指头的手从货架上夹下来一个,一手捏着父亲递来的钱,一手笑着把火机放在柜台上推到我跟前来。第二家铺子的女人精干实在,讨上两句好话才舍得白白送上一个火机;可她家做出来的豆腐和豆皮儿却很爽口,黄豆量足,母亲看见若是有新做出来的豆腐、倒也会买点儿回去。
我们家的祖坟多在爷爷院后的一个河洲上,大概是前人挖出来的,不得而知。爷爷家里种田、不打渔,以前养过鸭子,可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所以家里便没有船也没有篙。去河口向谁家借根长篙,邻里间打声招呼倒也方便得很。河口零散地停着大小不一的水泥船,铁栓儿散漫地扎在岸边河泥的斜坡上。爷爷随处拔开一条小船的铁栓儿,便招呼着要到河洲上烧纸的我们上船了。这条河抱着整个村子。爸爸说起过他那时候曾和妈妈在这河里捞螃蟹、捞龙虾,脸上还是挂满了温馨。如今的河里堵着些垃圾,透着河面也能望见恣意蔓延的水草了,爸爸这么说,却只能不住地勾起我漫天的联想来。
爷爷安稳地立在船头,父亲沿着窄窄的船沿儿向着另一头走去倒也淡定得很,可我每每却总是担惊受怕。爷爷细心地铲去舱里的水,我和母亲便把一捆捆纸铺在船梁上,坐下我才会安定许多。爷爷撑起长篙,船儿捋着波浪奔向河洲。到了河的中段儿,河水仿佛才干净了些。若是赶上了晴天的日子,开阔的水面上,粼粼的波浪随着清风荡漾。极目望去,黄灿灿的油菜花儿惹得白色的蛾儿竞逐,绿油油的麦苗儿也窜出了地面儿,把天际都染成了一片模糊糊的青绿色。园子里也随处可见鹅黄色的连翘儿,恍惚间仿佛我又置身在齐腰的油菜花丛中了,徒增一抹哀伤罢了。
船靠上岸,河洲上密布着坟茔,却也夹杂着种满了油菜花。只有跟着爷爷和父亲的步伐,我才能从蜿蜒的一脚宽的田埂里辨出我们的目的地来。几处坟茔多是砌上水泥,有些还用砖瓦搭出个避雨的小屋儿来。可是即便是这样,在水泥裂开的细小的缝儿里,都会有一两根倔强的草冒出来。烧纸磕头都是肃穆得很的事情。父亲用百元的纸币轻轻抹过一叠叠纸,便当是给祖先所谓阴间的馈赠了。火光吞噬着递来的一沓沓的纸,谦恭的人们在坟前模糊的亮光里依次磕头合揖,以这样远古而传统的方式寄托着些不可名状的忧愁和绵延的思念。
可离乡的人不再固执地要求葬回乡土里了。那些远行的年轻人也抛弃了故乡的牵念、成了漂泊在另一个新的世界里的孤儿了。于是,芜杂的荒草窜出废弃的墙根儿,笼罩在被废弃的坟头上了。小时候我喜欢呆在的这个村庄里,小卖部里会有讨孩子们喜欢的各种玩意儿,气球、十八般兵器,还有一踩便出响儿的一粒粒的小花炮儿;直到那个会陪着我们一起玩耍的、古怪精灵的年轻的老板也有了皱纹时,我才恍然发现、听不见孩童回荡在整个村子里的欢声笑语了。而我,也执意背起了行囊,极力地擦拭着我身上来自这个村庄的标签,成为逃离的人中的一个了。
就连那炊烟,都不愿意陪暮色慢慢老下去了。
冬眠:搓背匠
手艺人多称匠,如木匠、瓦匠云云。艺术者也多喜欢用“匠”字,所谓匠心独运,大概也是对有所修为的人的一条颇高的评价了。对很多行业的从业者而言,称之为“匠”,多是因为其符合前一条的。家里装修,“木匠”、“瓦匠”、“漆匠”这些都是家乡里听惯了的称呼,乡音读来,无非是“匠”字变成了“呛”,可倒是倍觉得亲切的。对于手艺老道的人,人们便也不唤作“呛”了,喊一声师傅、递上一根烟是基本的规矩,“师傅”大约是一个极高的评价了,可是多用于敬称后便渐渐司空见惯了,倒也不似以前、像捧着个青花瓷的碗一样随时怕磕着摔着了。
李佩甫的《生命册》中有个刻画的惟妙惟肖的人物,名字叫做梁五方,揽得一手上好的木匠活,竟连上梁都能一人做到;可树大招风,惹得周遭的人记恨,可谓最是落寞。这样的人,叫一声“师傅”是无妨的——技艺高超,乃至已是佼佼者的地位了。可为人不厚道、仗着些过人的本事便觉得能两脚生风的,确实是很多“师傅”的作为。这时,若是从我的一丝私念出发,称呼那些有着高超水准却又谦和的手艺人一声“匠”,还是觉得心满意足的。匠者仁心,这里“匠”的称呼我却宁愿取后一种释义,专注于技艺本身而已日臻精致到完成一件件艺术品了。不准确了些也罢,这里要说的搓背匠,大约就是我的生活里不常遇见的后一种“匠”群体中的一员。
搓背是澡堂子文化的一部分。公共澡堂,在有着寒冬的地区大概是司空见惯的。寒冬总是让人要么躲在被窝里,要么蜷缩在几层厚厚的衣服里,过上几日就觉得身子不自在了。下澡堂尤以午饭后最佳,热量足、水也干净。进了澡堂,朦朦胧胧的水汽氤氲在整个屋子里,便觉得恍若仙境了。大池子里滚滚的热水是人们的最爱,无论尊卑,无论胖瘦高矮,反正大家都是一丝不挂,何必拘谨那冠冕堂皇的一二三。
澡堂是一个片区里最好的社交场所,平日里见不着的邻居朋友,竟经常在澡堂子里撞上面。于是新来的澡客与池子里的人们大多边是闲侃着、边慢腾腾地钻进蓝色的热水里,懒洋洋地像喝醉了酒一样每个毛孔都舒展开来,恣意地享受着压抑许久后奔放的快感。非得烫到全身通红、连脸颊都变得红润起来后,大家才会心满意足地再去淋浴。古时称热水为“汤”,以热水浇雪称为“沃”雪。我是喜欢极了这两个字的。尤是再结合现在的意思,更是有趣。在热水里,人们便像是一块块小火慢炖的排骨,仿佛出锅便如同是醇厚的排骨汤般美味,连每一粒骨髓都会随着热水沸腾起来。在舒坦的热水里,大约人们即便是被慢慢炖成酥而软的骨渣,许多澡客也是心甘情愿的。而与此同时,澡客们又像是一块块肥腴的田地,单是这“沃”字听来,便瞬间觉得身体上下滋润了不少、连心口都是暖透了的。
只有在热水里烫得舒坦,搓背时才会倍加逍遥。毛孔都痴痴地长大了嘴,污垢便少了藏身的去处。粗糙的澡巾细细捋过每一寸肌肤,身上的泥灰便聚成黑而黏的澡垢了。在家乡这一片区的方言里,这种脏东西有个令人嫌弃而生动的名字,读作“啃”字的第四声,即与“掯”字同音。家乡话里入声多,短促而有力的“掯”音读来,便觉得是一种人人都厌恶而急于抛弃的东西了。而我常去的澡堂子里只有一个搓背工,便是那位看着我从幼时到如今的搓背匠。
说来惭愧,并不知道这个搓背匠叫做什么,父亲和一些同辈的人多称他“八爷”,连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也都唤他作“八哥”,如是便可见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八爷是标准的家乡人,浓眉,国字脸,操起乡音来比他的搓背技艺还要熟悉。父亲从澡堂子的前台买来擦背的筹儿,进了澡堂便把那窄而厚长的木片儿顺手递给了八爷,算是排队擦背的凭证。若不是年关赶场子,等到我们慢悠悠地从汤池子里爬出来,歇着喘上半口气,便正好轮到我们搓背儿。热水刚把身子骨烫得酥软,正是搓背儿的最佳时候。澡客坐在石墩上,澡巾在八爷厚而不蛮的力气下却温顺得很,顺着肌肤上下、一一停驻。喜欢和澡客打着趣儿的八爷并不省力气,也没有花哨的技法,可朴实厚重的技艺却是实实在在地让澡客潇洒。岁月的年轮轧过他的面庞,曾经的壮年如今看来竟也有了叠叠的皱纹,尤其用力时候、若是望着他的额头,便可直直地看到在灯光里反射出的满满的亮光,顿生唏嘘。可他憨厚而爽朗的笑却依旧不减当年威风,竟也让我猛然觉着自己仿佛还是个孩提。
离乡多年,偶尔回乡,即便已经搬了家,可我最念念不忘的事儿之一便还是那个片区里八爷的搓背功夫。前几日去澡堂,竟觉得八爷讷言得多,气氛也生闷不少。大约是我再也听不懂周围邻居们的闲聊了吧,大约是我再也看不懂八爷的笑了吧。住在那里的人也是愈来愈少,很多的人也喜欢去更舒适的所谓浴城。可我不喜欢。灯红酒绿的浴城里与水汽一同挥发的、充斥着的躁气让我拘束。于是偌大的澡堂子里,视线里年轻人的模样竟渐渐模糊。大约是水汽蒙住了我的眼吧。我默默地想着。
八爷说,这样的澡堂子只有咱们里下河地区才有,这背功都是扬州府的技艺。我不信。我的印象里,固执地认为北京也应当有颇多的澡堂子,是那种皇城根下提着鹦鹉、攥着蟋蟀的澡堂子。可满目的高楼却让我一时恍惚错乱。“大概北京的老胡同里还有你说的澡堂子吧。”有人这么劝我。
可我从来没有去胡同里找过。
我知道,我找不到。
四时:报亭纪事
“伢儿,《扬子晚报》涨到七毛钱一份咯!”报刊亭的老板娘笑嘻嘻地说道。她对我笑得总是非常热情。我攥紧了手中的五毛钱硬币,努着嘴在报刊亭前想了会儿,正准备悻悻地走时,老板娘又仿佛带着份得意地说道:
“今儿五毛先给你,明天那份给我一块钱就好。”
我飞快地摇着头:“不成,那样我可亏了一毛钱。”
“嘿,你这小子,机灵倒是机灵得很。”老板娘说着便把一份报纸递给了我,见我迟迟不伸手,“明儿找你一毛不就行了。”说完便又是笑嘻嘻地从我手里接过钱、把报纸捅进我的怀里。
小城里报亭的制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正方体的铁皮盒子,延伸出的顶棚刷着亮绿色的漆,背面贴着两面落地的透明玻璃,好让来往的人看得清报亭主还没卖出去的旧货——偶尔这里头也是能淘到宝贝的。往日里报亭一侧的防盗门总是锁住的,唯有正面打开的铁皮窗可以通晓内外——支开的三面铁皮几乎是报亭的全部门面,竖立的两面整齐而密集地垒着一层层杂志,平放着的则往往是日报或是周报——除了新闻类的晨报晚报,更多的是每周发行一刊的奇闻杂刊。透着支出去的铁皮留出的空间,报亭主们慢悠悠地迎接着来往的客人。在小城里,报亭是小社区中为数不多的公共设施,于是往往在那里遇见的都是熟客——每天都特意来捎上一份日报的,聚集在报亭旁一支烟能玩一下午扑克牌的,在彩票开奖结果前侃侃而谈的,抑或是只是单单在聊天唠嗑的、话家长里短的。彼时的报亭,对于人们而言,或许是可以称之为生活的,是不少人日常不可或缺、而又往往能迸发出精彩的存在。
初中时的我曾负笈求书。刚进入新城市的我仍然对报亭有着近乎偏执的执念,就像是不可或缺的依托似的。住校的第一年里,校内有个不大的报亭,无所不能的小报亭承载着住宿男生们的难得的骄纵——繁多的零食与饮料,丰富的篮球杂志,以及随时可以借到的篮球。在那个闭塞的环境里,小报亭那“买一送一”的饮料瓶盖、那干脆面里新奇有趣的卡片,往往总是教室角落里难得的轻松与欢愉。
这种充满依赖感和自我放纵的欢愉戛然而止于某一个时刻——但我对于报亭的好感却丝毫没有消退。在外租住的小区旁就有一个报亭。那时的晚报已经是一块钱一份了。周初,我给那报亭的奶奶一张五元的票子,这样每日便都顺路笑着取走一份。奶奶虽热情,但却也是个悭吝的生意人,偶尔的精明刻薄倒是让我很不舒服。
又过了一年,便搬了家。家前的那个报亭里是个中年男人,总是一副懒洋洋的模样,讨嫌而冷淡地拒绝着宾客额外的要求——大概很少有常客的缘故吧,慵懒的人不知怎的、与这繁华的马路配得很。也是在那一年,我开始从母亲那个小小的手机屏幕里,翻阅着每月十兆流量所给我带来的文字讯息——或许正是这多重的缘故之下,每日的晚报倏地就从我的生活中变得无足轻重起来,和那个变得慵懒的我相似极了。
高中时候我去了城南。城南的新城宽敞了不少,整齐的小区与店面、穿梭流动的人群,和再也没有人依赖的那一顶顶报亭。新家的附近,有两处报亭。一处在学校南门对面,两个精干的女人最喜欢进各式各样的作文素材的杂志——那往往是卖得最好的,家长和那些勤勉的学生尤其爱买一些新鲜的作文期刊。一处在路口一角,那个店面我倒是没有很深的印象了,只依稀报亭旁晚上最是热闹,报亭后头的那个排挡,每晚总是能看见三三两两的人醉着酒。那几年里,我再也不看日报了——那曾经让我心心念念的日报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就像从没有来到过我生活中一般消失了。
再后来呀,我就到了园子里。园子里报亭不少,各种卖着期刊的地方也不少。期刊也卖,可卖得最多的还是各式的校园纪念品与饮料。在那熙攘的人流中,报亭仿佛变成了被遗忘的站点,或匆匆经过、或匆匆停留,我倒是再也记不清那报刊后的一个个面庞;连曾经必买的杂志也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终归是有了更值得人忙碌的事情了,终归是不再有所牵念于一片小世界了。
直到园子里的报亭彻底地消失在我的眼睛里的时候,我才猛然想起,那随着我生长的报亭,终于也将在执拗之中落幕。
小时候,那个我常常买报的报亭离着家里的小店铺不过十几米,从店铺到路口、再蹦着穿过小城南北向的主干道,另一侧路口旁的报亭便出现在我面前——那个陪伴了我十年的报亭现在仍然在那里,可是周围的环境却早早变了个样。国庆回家时,街道两旁竟变得陌生了起来。小店铺旁,那栋小城里一度最亲民热闹的三层超市装潢成了化妆品卖场,门口顶着碗的杂技艺人在稀稀拉拉的围观人群前、在聒噪的车鸣与迷蒙的扬尘里战战兢兢。我回去时曾路过那报亭,向着黯淡的报亭里望了一眼,只见有人低着头、沉闷地玩着手机,应当早已不是那老板娘了吧——我印象里的她,是绝不会容许这喧嚣与繁华节庆里、窝缩在小城一角的黢黑里的。
成长所延伸的触角也愈来愈远——
稚童在成长,故乡终归逐渐渺远,而他也需要去远方流浪;
社区在成长,报亭那小城里曾经仅有的公共设施,逐渐消弭、逐渐沉沦,变得再也不那么唯一,变得再也不那么让人感到依赖;
人群在成长,即便是小城里最执念于一方土地的人,也开始了穿梭,成为熙熙攘攘的一份子;或许再也没有人记得他那清晰的面庞了,那笑起来就抖动的、严峻的法令纹逐渐融化在薄薄的脸谱里;
连世界也在成长,几页报纸里那黑色油墨所勾勒出的大千世界,变成了屏幕另一端更为缤纷的存在了。
故土与小城,就这样一点点地模糊、一点点地消失。就像那模糊的、消失的我一样。
报亭终究成了一门生意。
我谨小慎微地穿行在小城的道路上。那一片我曾经尽情吸吮着营养的土地,变得越来越模糊。有次回家时,曾想去常去的澡堂子会一会八爷,却被父亲的好友拉去了新开的浴城——我开始娴熟于浴城老板的应承和不符实的夸赞,在朦胧的水汽中怡然自得。在觥筹交错的酒席上,我越来越注意祝酒词和敬酒时该说的话,再也不会犯一些让整张桌子洋溢着欢乐与成为津津乐道的说辞的幼稚错误了。小城,终究不是我从小成长的小城了;而我,也终究不同于过去二十年的那个我了。
离原来家里那个小店铺向北一百米,有一家卖了二十多年日用品的小店。小店的老板姓吴。五十多岁的他憨憨地笑起来时,已经有了厚重的皱纹。“伢儿,学校里好不好玩呀?认识朋友了没有呀?是女朋友咯?”
我仿佛看到那个十几年前的平凡的黄昏里,那个涨红着脸的孩子努着嘴争辩道:
“女生的朋友,可才不是女朋友呢!”
感谢姜伟峰对本文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