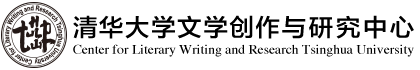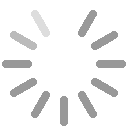首期“清华大学国际文学工作坊”举办
2017.07.17
2017年7月15-16日,清华大学“国际文学工作坊”第一期在凯风公益基金会会议厅举办,主题是“《望春风》与格非的写作”,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和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访问学者森冈优纪、日本立命馆大学的秦劼教授、韩国西江大学的李旭渊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的Paola Iovene教授、多伦多大学的孟悦教授、台湾清华大学的吕正惠教授,以及来自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和其他高校的专家学者20余人参加了此次工作坊,并围绕会议主题展开深度研讨。活动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王中忱教授等主持。

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举办第一期“国际文学工作坊”
15日上午工作坊正式开始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格非简要介绍了中心举办此次“国际文学工作坊”的初衷和意旨。随后,王中忱教授主持并介绍了上午发言的四位嘉宾。
首先,森冈优纪和秦劼教授以“流转的时代与故乡——从《望春风》的叙事来考察”为主题展开讨论。森冈优纪表示,自鲁迅的《故乡》以来,从知识分子的视点描写故乡(常常是农村)一直是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故乡》的叙事者“我”和闰土之间距离很大,叙事者时时流露出的现代意识和小说中描写的农村情景,形成或明或暗的对比,这种叙事模式,成为现实主义小说描写乡村时常用的模式之一。相比之下,格非的长篇小说《望春风》完全脱离了这一模式。森冈优纪根据小说章节依次考察了《望春风》的叙事风格是如何脱离这一模式的。她说,《望春风》没有像八十年代先锋小说那样去解构旧有的叙事模式,而使用了一种新的叙事方法。小说的前半部分主要运用边缘性的少年视点叙事,这和八十年代的先锋派小说有很多共通点;小说的后半部分的叙事更加复杂,既有不同人物的第三人称焦点叙事,又可以看到鲁迅以来的知识分子叙事人的第一人称叙事;后现代的元叙事,则贯穿全篇。在小说中,这三种叙事方式灵活转换,在鲁迅以来的“知识分子叙事人对古老的存在”这一主题上进行了全新的突破。秦劼教授则使用了数理统计方法,初步计算出《望春风》中出现了至少99个人物,其中67人有语言对白,为小说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分析探索方式。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旷新年教授以“农民可以说话吗?——格非《望春风》门外谈”为题,从自己的农民身份认同谈起,对当代知识分子的新启蒙主义立场进行了反思和批评。解志熙教授则以“乡土中国的文学纪传——《望春风》漫谈”为题,就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作品反映了作家自身的乡村经验和对乡土社会的关怀。在格非笔下,无论土改还是文革都没有摧毁乡土中国,倒是推动了乡村的建设,带动了整个中国的发展,反而是市场经济给乡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巨变。从小说艺术方面而言,跟格非早期的先锋派创作相比,此次格非的写作渐渐回归到中国古典叙事艺术的倾向,各章节的写作有纪有传,纪传互文,很有章法,又蕴含丰富内容,提高了读者的阅读趣味。此外,小说亦保留了格非早期的先锋派写作特色,一方面有延续,一方面有新变,但他认为两者没有很好的融合,希望格非在未来的写作中能让“延续”和“新变”更好的交融。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生林培源以“重塑‘讲故事’的传统——论格非长篇小说《望春风》的叙事”为题发言。他将《隐身衣》比作“江南三部曲”之后的一曲余音,而《望春风》则像是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两者所叙之事虽然迥异,但是无论小说的叙事技巧,还是对社会现实的关照,都有或隐或显的关联,这种关联不妨看作作家在“江南三部曲”跨越百年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之后,朝小说这门讲故事的技艺向内转的一个努力。他从说书人的角色跟叙事交流、史传传统跟原小说的关系、“重返时间的河流”等三个方面探析了小说是如何重塑讲故事的传统。
15日下午的工作坊由解志熙教授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贾立元共同主持,有六位嘉宾发言。
首先发言的是李旭渊教授,他的主题是“对乌托邦的渴望与Virgin Mother的想象——兼论韩国人眼中的中国小说与格非小说”。他首先介绍了格非的《人面桃花》在韩国读者中的阅读情况,读过的韩国读者普遍认为这是一部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作品”。随后,他借由小说中“乌托邦”和“陆秀米”的形象为切入点,以《诗经》中的姜嫄、西方神话中的圣母玛丽亚等形象展开论述,从处女母亲(Virgin Mother)的角度解析了格非的写作。他认为,《人面桃花》是一部描写在乌托邦的生产和毁灭之间不断轮回的小说,是一部关于普遍意义上的“人”的小说。格非在《人面桃花》中的写作超越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以乌托邦为关键词,探讨了人类最根本性的本能和宿命,小说跨越了国界,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具有了普遍意义,这也正是它成为优秀小说的原因所在。
吕正惠教授从“古典化的现代叙事”视角分析了格非的小说叙事里的古典意蕴。他以《望春风》小说开头部分为例,指出格非恢复了中国古代文学很特殊的文字表述方式,显示了独特的魅力,而在小说中利用意象的复现来推进人物命运的写作技巧,在现代小说家里实属少见。格非既熟悉中国古代的传统,又熟悉西方的叙事技巧,两者融汇,柔和起来,实属难得。
孟悦教授的发言主题是“荒废与‘城为天’时代的价值”。孟教授认为《望春风》让她对当代中国农村的变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农村的荒废,更加反衬出现在是个工业化、城市化加剧的时代,农业文明成为失去价值的残余之物。格非的小说对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有着不同寻常的表述,强调了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以及意义和价值的延续性。她认为小说对“父与子”、“我与春琴”之间的描写,让读者意识到生命或者历史是大于个体存在的,这让小说的历史感和时间的意义变得非常浓厚。最后,她觉得《望春风》是格非一系列新写作的起点,希望在他未来的作品中看到更多细节化的描述,为现代生活在“城为天”中的人们留下更多过去的痕迹。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张翔以“后革命时代的虚无感”为题展开探讨。他认为,对当代人虚无感的深刻揭示与细致描绘,是格非“江南三部曲”以及《望春风》作品非常重要的特征。他以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为例,从三个方面展开阐述:第一个方面是小说里对虚无感现象的描述;第二个方面是小说里对革命的画面感的叙述;第三方面是市场时代的无意义感。最后,张翔以对小说中的“我朝东边望了望”这首诗的分析结尾,最终只有春风在那里吹。小说通过这种方式提出了一个深刻问题,即故乡复活的社会基础在哪里?这个空洞的能指在这里,但是没有所指。他说,现阶段中国的特点并非只有虚无,但未来的契机很模糊,小说对这种复杂性的把握精准,刻画入微。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何吉贤分享了对格非作品的阅读经验。首先,他认为尽管乡村已经在现代城市的扩展中面目全非了,但仍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镶嵌寄存在一些人的经验或记忆当中,不管是以幻觉还是以碎片化的记忆,或者说某种情感的转化等等形式存在。《望春风》在当代呈现激烈变化的大背景下,所展示的现象、所刻画的深度都令人瞩目。他进一步将视角缩小到“村庄叙述的角度和传统”展开分析。其次,他讨论了文体融合的问题。他说,小说的写作在一定意义上要跟中国式的中国叙事接上,而且形式上的探索也要在很多新的领域展开,在这个方面格非的探索和独特性的贡献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陆楠楠分析了《望春风》的叙事意图,描述作者在形式探索上面临的危险。首先,她认为小说开始便设置大量人物出场具有一定危险性,针对这个问题格非采用了齐头并进的写法处理复杂的人物关系,类似本纪和列传并至的写法。小说最终构成了一个文体,读者看到的是全面铺开的网状的叙事结构。第二,格非采用了设置悬念的方式提高了小说的可读性,比如父亲过世的悬念,包括母亲的悬念,也包括“我”和春琴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揭示悬念离提出悬念的时间太长,也具有一定危险性。针对这点,除了悬念,整个小说的抒情性也是推动读者阅读的重要动力。第三,小说里情感的投入也是危险的。她认为小说中作者和读者还是保持了一定距离,格非找到了他自己想要保持的均衡。

清华大学“国际文学工作坊”首期活动现场
16日上午的工作坊由孟悦教授主持,有四位嘉宾发言。
Paola Iovene教授以“我的归程:格非《望春风》初探”为题对小说进行了深度剖析。首先,她讨论了《望春风》与当代史、乡土文学和格非其他作品的关系。其次,她主要分析了《望春风》与世界文学的关联,即小说开篇引用的意大利诗人蒙塔莱的作品《也许有一天清晨》和荷马史诗《奥德赛》。她表示,蒙塔莱诗中对世界的虚无性的发现,能在《望春风》中找到对应。格非与蒙塔莱诗中的主人公一样,都面临着坦白这一发现和保守秘密之间的矛盾。最后,她认为一篇小说不仅仅只讲述已经消失的过去,还会提供针对现在与未来的想象性解决。《望春风》最后重返田园,事实上小说的叙事者也并不真的认为乡村能够起死回生,但小说提供了关于幸福的可能性,或许隐藏在趋利体制所进行的拆毁和重建之间的某些缝隙中。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贾立元分享了他阅读格非作品的感受。他表示,农民是很会讲故事的,《望春风》是一个农民讲的故事,这并不只是作者本身认同自己农民的身份,而且叙事者“我”和春琴也是两个农民,在大的历史动荡之后留下的废墟之上讲述了一个关于消失了的村落的故事。小说尽管保持了作家一贯的迷宫气氛,人物命运错综复杂,推动人物走向最后结局的力量也是不可预料的。但是,扑朔迷离的背后隐约有一种确信,他认为“确信”的对象是一种命运的共同体,具体到这个故事,就是“乡村、社群共同体”。他认为,叙事者以一种地方志的方式,努力的想要存留一点风土人情的点滴,让其不至于荡然无存,体现了作家自觉的使命感。
中国计划出版社编审西渡发言的主题是“漫长的告别”。他从自身经历谈起。身为农民,他认为自己从来没有摆脱过农民的意识,没有摆脱过这种浓重的乡村色彩,没有摆脱过自己对于乡村的眷恋。格非的小说写出了一种“乡村知识分子”的想法,他的身体已离开乡村,但他的心理上还保留着农民的乡村情结。对于这一代乡村知识分子来讲,这个告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认为,在格非的小说里,这种漫长的告别被形式化了,并着重分析了小说的第四章中出现的五次“告别”。
作为最后一个发言嘉宾,王中忱教授表示格非小说中的人物,包括叙事者,都身处特定的历史激流当中,而不是激流之外,这是与社会科学家的乡村叙事很不一样的地方。身为作者,格非也把自己,把叙述者,把人物都放到那个历史的进程当中,设身处地的去想像在那个激流当中,在那个进程当中人的感受。这一点是特别有魅力的。此外,他也对作家深受现代主义影响从而过于注重小说结构的完整性、人物命运的前后呼应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随后,格非教授感谢参会嘉宾的发言,并对参会者提出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最后,专家学者们围绕主题进行自由讨论,并对中心未来工作的展开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工作坊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注:部分论文已经发表在《澳门理工学报》2018年第21卷第1期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