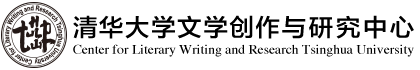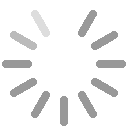清华文学研究 | 王中忱:艺术追随帝国,抑或帝国追随艺术?
2020.06.25
“清华文学研究”栏目旨在推介清华学人在文学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促进学术交流。
此文是王中忱教授最近出版的《现代文学路上的迷途羔羊》(作家出版社2020年4月)一书里的“小引”,收入该书前未曾发表,副标题为作者新加。感谢王中忱教授授权发布此文。

艺术追随帝国,抑或帝国追随艺术?
—重释日本现代文学史的一个视点—
1、后发型新“帝国”及其言说的特征
本书所收文章,选自笔者已发表的有关日本文学的论文、札记或随笔,所涉及的时间范围从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大体相当于中文学界所说的近现代和当代。
同属于汉字圈的日本也使用“近代”、“现代”这样区分历史时段的概念,但日文脉络里的“近代”迻译到中文应该怎样表记?一直是令人困扰的问题。在实际翻译中,原样挪用者有之,加以改换者亦不少见。如中国媒体上频繁出现的“现代化”,迻译至日文多会变为“近代化”,而日文中的“近代”迻译至中文则常被写为“现代”,与本书内容相关且比较切近的例子是柄谷行人(1941- )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如所周知,此书中文版题目里的“现代”在日文原文里实写作“近代”[1],如此改换,应该是译者的有意而为。
但以中文的“现代”置换日本的“近代”是否就恰当妥帖?已经有研究者讨论过,尽管同属于汉字圈,尽管字形完全相同,中文和日文里的“近代”含义却很不同。这不仅因为作为历史分期的概念,中日文里的“近代”各自所指涉的时段不能完全重合,更因为中国和日本的“近代”经验和认识存在巨大差异。伊藤虎丸(1927—2003)援引竹内好(1910—1977)《现代中国论》有关“东方的近代是西欧强制的结果”的观点,分析“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的“被近代化”经验以及由对抗“西欧强制”而产生的“主体性态度”,批评日本自外于亚洲,毫无抵抗地“把自己置于西欧的立场”的“近代”观,实际上是文化主体性缺失的表现。伊藤指出,正是基于这样的近代观,在日本会较多从“肯定的意义”上理解“近代”,并“认为‘近代’与‘现代’是连续的,较少有人意识到或主张将其做明确的区分”[2]。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把日文的“近代”原样挪到中文,固然会在抹去翻译痕迹的同时遮蔽中日“近代”经验和认识的差异,而用“现代”置换“近代”,则难免淡化日文里“近代”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意涵。
需要注意的是,上引竹内好和伊藤虎丸的中日“近代”比较论,是从二战以后反省日本近代历史的视点,分别针对冷战及后冷战的时代状况而发的,并且,和所有的宏观比较论一样,为了论述的方便,他们都把讨论对象做了简约化甚至本质化的概括。如果我们把关注点从比较论收拢回来,聚焦于日本近现代历史的研究,或者说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全球史背景上,则不难看到,何谓“近代”这一问题即使在日文脉络里也众说纷纭。所谓“近代”,自然首先是从时间的维度,在表现和此前时期/时代之区别的意义上确立的,而在有关日本历史的叙述中,“近代”起自“明治维新”,可谓一个共识,但“明治维新”的起讫时间应该怎样确认,研究者间的看法即颇有歧异。
成田龙一(1951— )考察二战以后日本学术界就“明治维新的起点”问题提出的各种观点,首先提起了远山茂树(1914—2011),他说:远山“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从底部结构(经济)决定历史的立场出发,首先把幕府末期的经济视为工场手工业的阶段,在此基础上看到各雄藩‘向绝对主义倾斜’的趋向,认为天保时期推进改革的主体成为了明治维新的政治主体。总之,是在把幕府对应着封建制之新阶段而推进的政治、经济改革—亦即失败了的天保改革和雄藩的成功改革进行对比之中,对明治维新进行阐释的”。成田认为,远山实际是把“欧洲近代的诞生—从封建制解体到近代诸关系和制度的生成之过程,和明治维新叠合了起来,期望由此找寻到近代日本的出发点。其认识的前提是:相对于江户幕府=近世封建制,明治政府=近代的中央集权制和资本制”。因此,远山及赞同远山观点的学者大都把“明治维新的起点放置在天保时期(1830年代至1840年前半期)”[3]。同时,成田龙一还举出芝原拓自(1935— )作为另一种观点的代表,认为芝原率先提出“世界史中的明治维新”问题,把关注重点转移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的东亚危机与变革,自然就把佩里来航(开国)看作了明治维新亦即“近代”的起点[4]。概言之,这两种观点或可概括为“内发型近代论”和“外来冲击型近代论”,尽管两者都有自己的论述依据,但从他们的分歧恰恰可以看到,如何确定明治维新的起点,其实涉及到如何解释日本“近代”的历史,不同观点牵连着不同的解释前提和观察框架,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史实。
关于明治维新的终结时间也同样如此,据中村正则(1935—2015)考察,关于这一问题“本来亦无定说”,大约至1960年代以后,“则有以1890年前后的明治宪法体制、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引用者注)为明治维新终结期的观点出现”。中村认为:“这些认识虽然和明治同时代人把西南战争和维新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之死视为明治维新终结的认识有很大差异,但从明治维新所设定的课题来看,其目标并没有停留在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是包含着国民国家的建立和经济的对外自立,这些课题的基本解决,确实是在日清战争和产业革命达成的时期”[5]。
中村本人是赞成1960年代后渐成通说的观点的,他们都把明治维新看做了一个充满了多种可能性的动态历史过程,认为到中日甲午战争,“明治国家”的格局和路向基本确立,也意味着这一动态过程的终结。中村等人注意到,“明治国家”既具备近代民族/国民国家(Nation-state)的品格,也带有帝国主义(imperialism)的性质,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把甲午战争设定为一个历史时段结束的标识,应该说表现出了一种洞见,但在此基础上显然还应进一步讨论,在全球史的视域里,明治日本所确立的国民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否具有自己的特性?其特性具体表现为怎样的形态?
一般说来,帝国主义行为主要表现为某一国家在本国领域之外推行的军事扩张和政治、经济、文化的统治或控制。这当然是可追溯到古代的历史现象。但在欧洲,由于经历了一个传统帝国因众多拥有主权的民族/国民国家的兴起而解体的过程,“帝国”(empire)与“国家”(Nation-state)的概念也便常常被放置在前近代和近代的对应关系上理解和使用,而在近代民族国家基体之上崛起的欧美列强,伴随着资本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则又明显表现为重返帝国的冲动,且在扩张动力、扩张规模与扩张方式的多样化方面,都远远超过传统帝国。据相关研究:“帝国主义”(imperialism)是在“19世纪中叶之后才形成的词”,在“英文中的imperialism与具有现代意涵的imperialist在1870年后才大量使用”[6];而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从这时期起,欧美列强开始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全面推行了殖民地统治”[7]。爱德华·萨义德(1935—2003)曾引证相关文献指出:“在1800年,西方的势力声称占有全球百分之五十五,但是实际上是占有大约百分之三十五的土地面积,然而到了1878年,此一比例已增至百分之六十七,每年以八万三千平方英里的速度增加”[8]。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出现,正是对近代民族/国民国家型的帝国之特征恰逢其时的表述。
如果说,1870年代已经进入全球帝国主义的时代,那么,日本处于怎样的位置?在此也许有必要了解置身于历史现场的人物的感受和看法,这不仅因为其与历史现场切近,还因为历史事件本来也包括对事件的言说。前面引述的以甲午战争为明治国家走向帝国主义标识的观点,都属于后世学者之见,而作为当时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直接参与战争筹划、推动并主导了战后处理的伊藤博文在战后发表题为《列国的国土侵略主义与日清战争的意义》的演讲,则是历史当事人自我言说的一个代表性文本。伊藤说:
剑桥大学历史学科教授Seeley曾言:十九世纪是国民竞争的时代。余则欲更进一步,为由其所说列国国民竞争而产生的政治上之主义下一新名称,曰:领土开拓主义的竞争时代。挟强国之威,乘弱国之弊,掠地拓疆,虽有人说此乃因人口过剩、生产不足等社会病根而生,实则不过是以美名装饰其表而已。
欧美强国,如今正如虎狼争肉,侵吞剩余的土地,但日本的对清国之战,却非为缩小其疆土,而为促使其警醒,一战惊破清国之迷梦,仅为得东洋事由东洋人处理之便而已。而战争之结果,偶然促成的事实,却与列国于十九世纪所造成的大势所践履的主义若合符节:台湾归入了我国版图。
国民性(nationality),依美国之例而言,未必须由同一种族之民构成,而同一种族未必成为同一国民,同一种族亦未必会形成同一国家。国家必须是组织起来的,国家的组织是至关重要之问题。要求国民性的单纯,希望种族的同系,归根结底是由组织的难易而来的问题。[9]
不必说,伊藤博文的演讲明显带有为日本的帝国主义行为寻找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色彩,这也表明,“帝国日本”的创建并不仅仅是政治、军事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一种言说行为。伊藤有关日清甲午战争的叙述,无疑是明治政府“正统观点”的代表,但也从其特定立场,讲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特点。首先,伊藤已经注意到,十九世纪并非是一般意义的国民(国家)竞争,他所说的“领土开拓主义的竞争时代”,其实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国家竞相争夺殖民地的时代。第二,伊藤认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顺应时代大势而为,他并未对欧美强国的弱肉强食伦理予以赞誉,甚至可说是语含贬损,而由此强调日本加入“国土侵略主义”行列的后发性、被动性以及获得殖民地的偶然性,自然可以视为是为掩饰“帝国日本”对外扩张行为的说辞,但也应看到,这些说辞恰好表露了后发“新帝国”的言说特点,即善于渲染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性和悲情性。第三,值得注意的是,伊藤有关“国民性”或曰“民族性”(nationality)、“种族”、“国家”的阐释,明显超出了一般所谓单一民族国家的论述,无疑是把殖民地编组到“帝国日本”疆域之内放进了考量的范围。
如所周知,走上帝国主义之路的日本随后便一路推进,其“近代性”及“现代性”的追求始终和对外扩张的殖民冲动紧密纠结,如影随形。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在“帝国日本”的言说空间里,日本文学发生了怎样变化,做出了怎样的反应?而在二战以后,日本的文学家又是怎样面对“帝国”的历史遗产的?这是本书所收各篇文章试图探究的总主题。
2、帝国与艺术:殖民历史与多样的现代主义
小说跃升为最具主导地位的文类(genre),作为近代文学的一个世界性特征,也同样发生于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在此意义上,高山樗牛(1871-1902)发表于1897年的长文《明治的小说》,所论对象虽然只限于小说一类,但实际上可视为对明治文学的断代史式的总结。樗牛自明治二十年代后期开始活跃于文坛,明治三十(1897)年更以当时影响最大的综合杂志《太阳》的文艺栏主笔身份执评论界之牛耳,其意见无疑是有代表性的。
在论文的开篇,樗牛明确把明治称为“圣世”,并言:“王政复古,知识求诸世界。国民思想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小说也不再停留于旧时观念。最近三十年,影响我国上下人心的改革精神之激烈、周全,实乃古今内外之所罕见”。很明显,这把“明治日本”与此前的“德川日本”做了切割,将之视为具有断裂性的新旧时代,在这样的视域里,樗牛把明治三十年的小说分为三个时期进行评述:
明治初年至十八年是我所谓的第一期,此时的小说数量之巨称得上汗牛充栋,但大抵承袭德川遗风,不是效仿马琴、种彦的荒唐就是学一九、春水的鄙俚,再不然就是对西洋小说生吞活剥。作为明治小说,实在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作品。直到坪内逍遥写下《小说神髓》和《当世书生气质》,极言劝惩主义之误谬,始开写实小说之滥觞,举世皆靡然从之,小说界大旗变化一新。这虽是时势所致,但当时世人皆困睡于旧梦中,无人能从旧圈套中脱颖而出,唯有逍遥逆对滔滔时流,为时代之先导,可见其人见识超凡、聪颖绝伦。百世之内,逍遥在我国文学史上必占有独特的地位。
…… ……
明治小说的第二期是写实小说的全盛期,从明治二十年到二十八年前后,时间跨度约十年。
若溯寻写实小说的系统,则如前章所言,可追至元禄时期的浮世草子,其间一度被传奇小说压制,除三马、春水、一九等人戏作尚有一丝写实遗风外,至明治十八年时已然形影不存。但自从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面世后,写实小说崛起,迅速压倒了自化政[10]以来牢占垄断地位的传奇小说,成为文学世界的一股重要势力。而传奇小说在西洋小说的影响下也多少有些改善,虽然仍受部分人喜爱,但终归无力再与写实小说抗衡了。其中,二叶亭四迷的《浮云》成为了时代先锋。
虽然逍遥的《书生气质》的根本精神是写实的,但是文体、构思多少还有些旧式传奇小说的影子。《浮云》则不然,其思想、文字完全脱离了旧范式,是真正新时代的产物。《浮云》以人物性情为主,而非以情节为主,因此小说规模结构虽较传统小说狭窄,但其事皆基于人情自然,浑然如一有机体。
如上,正是在新旧对立的文学史构图里,樗牛肯定坪内逍遥的小说论和小说作品作为“时代之先导”的作用,特别是二叶亭四迷小说《浮云》的“时代先锋”意义。而他所谓的“先导”、“先锋”等概念,无疑都是在与“旧时观念”比较的意义上使用的,其实强调的是其“近代性”或“现代性”特色。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逍遥的理论还是二叶亭的作品,都和樗牛所构想的“国民文学”明显存在距离。在同文“序论”部分,樗牛提出“国民文学”的概念并这样予以界定说:“国民文学是国民性情表露的一种形式”;“表达国民之情感与希望者,乃谓国民文学”;“以国民性情为基础的文学将是永恒的文学,不朽的文学,它会与国民永存”。以此为标准,樗牛不仅对坪内逍遥和二叶亭四迷都表示了不满,更对进入第三期的小说加以愤怒呵斥。按照樗牛的划分,明治小说第二期为明治二十至二十八年,亦即1887年至1895年,而把1895年作为此一阶段的终点,樗牛无疑是考虑到了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在《明治的小说》结尾处他明确写道:
是时正当日清战起,越年而未息。一般文学被弃于社会关注之外,而这次战争给纯文学的影响,似亦未称深远。从社会上层至下层,在政治、宗教、学术上具有如此巨大影响的世界性战争的大胜利,居然于诗歌小说未发生多大关系,这是十分奇怪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民的审美意识是极匮乏的。我国文学家大都具有超凡脱俗的习气,以文学为出世之物,从不想着应该贴近人生世态,踏上与之共同精进之途。因此,在劝惩主义消沉之后,其结果却是写实的小说家和批评家同声褒奖art for art主义。以至于他们无视道德、宗教,将社会国家的时事问题排除在诗歌小说的题材之外。……王师越海西进,举国投身国家的精神大运动之际,除二三流作家作些浅近的战争谈之外,竟无一人歌颂这爱国义勇精神。不仅如此,倘有人写了关于战争的的著作,反被贬斥为媚俗之作,这着实让人无语。[11]
虽然樗牛在此没有直接点出名字,但从他对非功利性的“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以及“写实小说家”的批判,不难看出其矛头所向正是他高度评价的坪内逍遥一派。这与其说是樗牛观点的前后不一,毋宁说体现了他企图把被视为具有近代性(modality)特征的“纯艺术”组合进“国民文学”的努力,是对可能逸出国民国家整体格局的“文学”的收编和规训。而樗牛以“日清战争”作为明治小说第二期的终点和第三期的起点,特别强调以与这场“世界性战争”的关系作为评骘文学的标准,亦表明他所提倡的“国民文学”,并不能仅仅从字面上理解为一个仅限于国民国家境域内的文学,其中显然也包含了对“帝国日本”跨越国民国家边界行为的积极呼应。这其实也是很自然的逻辑,帝国性的视野本来就是一种具有世界性视野。
作为文坛主流的批评家,高山樗牛的意见应该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而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类似意见并不限于日本的文学批评界。如著名语言学家、1894年出任帝国大学博言学讲座教授的上田万年(1867—1937)即于同年发表《国语与国家》的演讲,首次把“国语”和“国家”作为一个有机的联系加以论述,认为“日语是日本人的精神血液,日本的国体主要由这精神血液维持”。而被视为日本“国文学”学科奠基人的芳贺矢一(1867—1927)在明治二十三(1890)年出版《国文学读本》(与立花铣三郎合著)不仅首先剥离与汉文脉络里的“文学”之关系,申明他们的“文学”是与近代西方“literature”相对应的纯艺术概念,且同时强调这种纯艺术的“文学”所应具备的反映“国民性”之特征,实际上从文学史论述的角度和高山樗牛的评论构成了回应。综合观之,在1890年代,亦即“明治国家”确立自己的基本格局和走向的关键时期,呼吁“举国投身国家的精神大运动”,已经成为包括文学在内的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声音和基本氛围。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里曾引用英国画家、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为反驳雷诺兹伯爵而写的一段话:“帝国的根基是艺术与科学,将之排除或贬低,帝国就不再存在。帝国追随艺术,而非如英国人所认为的那样:艺术追随帝国”。不过,萨义德所关注的重点,是帝国主义的运作是如何在“超越经济法则和政治决策”之外的“文化”领域发生,并由此出发去揭示一直被视为独立自足的文学文本“与真实背景的复杂关系”[12],所以,他没有去讨论布莱克所提起的艺术与帝国的先后次序问题。倒是W.J.T.米歇尔在《图像何求》一书里接过了这个话题,并进行了锲而不舍的追问:“如果乔舒亚·雷诺兹是正确的,艺术只能做的就是步帝国的后尘,贪恋新皇帝的宫殿。如果布莱克是正确的,那么,艺术和科学就处在一个更加复杂的位置”[13]。米歇尔明确表示自己“站在布莱克一边”,但同时补充说:布莱克的观点未必“会令艺术家感到欣慰”,因为“如果帝国追随艺术,那并不能保证它所引领的是正确的方向”[14]。
米歇尔的说法虽然有些缠绕,但基本意思还是可以看得清楚的,对于帝国和艺术究竟是谁引领谁的次序问题,我们其实不能过于计较,更不能做机械的区分,因为在实际的历史情境中二者关系曲折而复杂。如果按照矢內原忠雄(1893—1961)的分析,日本作为后发型或“早熟的帝国主义”,其殖民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来自“垄断资本主义的发达”,而更多来自“帝国主义意识形态”,[15]那么,“帝国追随艺术”或为常态,但本书第一篇文章所述及的二叶亭四迷,却提供了“艺术追随帝国”的实例。这位被视为日本近代小说言文一致体之开创者的作家,在1902年决然放弃学院教职和文学写作,只身孤旅前往中国,无疑是他早年被培植于心的“帝国主义的迷狂”膨胀发酵的结果,而他的“冒险”之举,又犹如行为主义的艺术表演,呼应了日俄战争之前日本国内日益高涨的对外扩张情绪。可以说,此一时期的二叶亭四迷既是“帝国日本”的追随者也是殖民扩张的自告奋勇的探路人,二者交织于一身。
在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段里,日本以天皇纪年的年号经历了从明治(1868.9—1912.7)到大正(1912.7—1926.12)、昭和(1926.12—1989.1)、平成(1989.1—2019.3)四次更换。如果说明治日本通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强行合并朝鲜(1910),确立了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格局和走向,那么,进入大正时期,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更获得了加速推进此一趋势的条件。大正时期常常被历史学家描述为日本近代历史上的民主主义高涨期,“大正民主主义”甚至成为指称这一时期的固定词语,明治以来一直由倒幕维新的强藩出身人物垄断的中央政府,1918年被民选众议院议员原敬(1856—1921)为首相的政党内阁所取代,以及1925年普通选举法的制定和实施,则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被视为标识性事件。但也就在同一时期,日本的对外扩张步伐也更为加快:1914年8月以对德国宣战的方式占领中国的青岛,把当时习称“欧战”的“一战”战火燃到了亚洲;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大规模地占有在中国的经济、军事权益;1919年残酷镇压朝鲜半岛要求独立的“三一运动”,深度强化殖民地统治。加藤周一((1919—2008))曾言:“所谓‘大正民主主义’,不是天皇制官僚国家的结构民主化,而是在帝国宪法制度下的政策民主化,也是自由主义的妥协”。[16]成田龙一在考察了吉野作造(1878--1933)等“民本主义”论者的言论后指出:这些论者“虽然在国内政治主张自由主义,却和国权主义结合在一起,容忍对外占有殖民地和扩张主义,难于和帝国清晰划开界线”,并明确说:此类“民本主义可谓是一个国家内的民主主义,那正是帝国的民主主义形态”[17]。而就近代中国的实际历史感受而言,“大正日本”带来的创痛是直接而切实的,其剧烈程度并不亚于“明治日本”,是全面帝国主义化的“昭和日本”的响亮前奏。
如前面已经言及的那样,帝国主义不仅仅表现为军事、经济的扩张,也表现为价值、思想、知识和情感、想象体系的建构,在此过程中,文学并不仅仅处于追随的位置,也表现出质疑和批判,本书论及的石川啄木、北川冬彦、中野重治,即为比较典型之例。而本书未能专题论及的夏目漱石,当然也在此之列。漱石留学英国归国后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后来在公开出版的讲义《文学论》的序言里指出汉文学意义上的“文学”与英语脉络上的“文学”概念之区别,并明确表示对后者的质疑,其实即是对发端于欧洲的现代意义的“文学”的质疑。但漱石并没有因此而远离“现代”文学,而是决然放弃学院的地位和职业,进入新闻媒体,以小说家的身份,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进行持续不断的批评。他的代表作之一《三四郎》里反复出现的“迷途之羊”的意象,显然不仅仅是在隐喻作品中人物的命运,更是对日益走向迷途的日本社会提出的警示。
不过,本书没有过高地认为这些文学家可以引领“帝国”转到“正确的方向”,在考察他们自觉与“闭塞的时代现状”严峻对峙的同时,也注意到他们在帝国的暴力控制之下所出现的游移、妥协乃至“转向”,分析了在帝国体制下文学想象和表现的可能性和限度,以及文学家们为克服其限度所经历的痛苦挣扎。中野重治和北川冬彦的文学活动都开始于大正末年,在昭和前期崭露头角。中野作为普罗文学运动的激进派为人所知,北川则以两份前卫诗歌杂志(《亚》和《诗与诗论》)重要成员的身份成为诗坛新锐,他们都怀持对明治日本时期形成的“近代”体制、成规的反叛意识,是自觉地与“帝国日本”的“近代”分开界限的“现代主义者”。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流的日本文学史叙述一直以所谓纯形式的“实验性”作为“现代主义”的标准特征,不仅由此把包括中野重治在内的左翼作家置于“现代主义”谱系之外,也把后来明显左转的北川冬彦从现代主义文学的正典(canon)行列排出。本书特别提出这两位作家的“前卫性”和“实验性”进行讨论,即是对此类文学史叙述偏见的有意矫正。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明治以来构筑起来的“帝国”也随之解体,但如何处理“帝国日本”的历史遗产,仍是相当沉重和严峻的课题,二战以后形成的世界冷战体制,更为处理这一课题增添了难度和复杂性。本书论及的堀田善卫、加藤周一、大江健三郎,都是在这样的历史状况中从事写作的作家,他们的探索更为直接地连通到当下。而自1930年代以来,日本文学已经和同时代的中国文学有了各种方式的互动,这既是日本文学史应该关注的内容,也是观察现代日本文学历史的一个有意思的视点,本书收入了与此相关的文章,即出自这样的考量。
注释:
[1] 柄谷行人《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1978年至1980年间连载于《季刊芸術》和《群像》杂志,1980年8月由讲谈社(东京)刊行初版。中文译本《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1月初版。
[2]参见伊藤虎丸《亚洲的“近代”与“现代”—关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初刊《二十一世纪》(香港,双月刊)1992年第12月号,氏著《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文学比较初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月,第7—10页。
[3]成田龍一:《近現代日本史と歴史学》,第25、24页。
[4]成田龍一:《近現代日本史と歴史学》,第22—26页。
[5]中村正則:《明治維新と戦後改革―近現代史論》,东京:校倉書房1999年10月,第14—15页。
[6]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3月,第226页。
[7]中村正則:《明治維新と戦後改革―近現代史論》,东京:校倉書房1999年10月,第12—13页。
[8] 爱德华·萨依德:《文化与帝国主义》,蔡源林译,台北:立绪文化有限公司2001年1月,第39页。
[9] 伊藤博文:《列国の国土侵略主義と日清戦争の意義》(明治三十/1897年4月的演讲),引自《伊藤博文演説集》,瀧井一博编,东京:講談社2011年7月,第64页。
[10] 日本的文化、文政时期(1804—1830年)。
[11]参见高山樗牛《明治の小説》,东京:《太陽》明治三十年(1987)6月号《太阳》;引自《改訂注釈樗牛全集》第二巻,姉崎正治、笹川種郎共編,东京:博文館1926年,第315-364,周颖译,未刊。
[12]爱德华·萨依德:《文化与帝国主义》,蔡源林译,第46—47页。此处所引布莱克的话参照陈永国、高焓译《图像何求》(W.J.T.米歇尔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第157页)做了改动。
[13] W.J.T.米歇尔《图像何求》,陈永国、高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第182页。
[14] W.J.T.米歇尔《图像何求》,陈永国、高焓译,第158页。
[15]参见矢内原忠雄《帝国主義下の台湾》,东京:岩波书店1929年初版。
[16]参见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下册,东京:筑摩书房2012年4月第11次印刷本,第442—443页。
[17] 成田龙一:《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シリーズ日本近現代史4),东京:岩波書店2007年4月,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