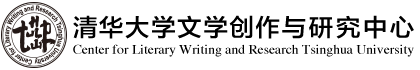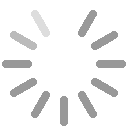贾立元:你最后的生存意志 ——关于《流浪地球》
2019.07.10
读刘慈欣的小说,会让我想到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关于文学之“重量”的讨论: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外部世界有着可怕的惰性与不透明性。世界和人们正在美杜莎的目光下石化这一凝滞、沉重的感觉,会对作家形成压迫,如果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他们笔下的世界也将随之石化。卡尔维诺由此阐述了他对“轻”的理解:通过盾牌的反射,柏尔修斯避免直视美杜莎的目光并将其杀死,作家也可以像这位英雄一样,让自己的作品以间接的方式切入生活而获得一种“轻”的质感,飞向另一个世界。他特别提到了《十日谈》中的故事:终日沉思哲学的诗人圭多·卡瓦尔坎蒂被一群看不惯他的豪门子弟包围,面对挑衅,圭多靠着自己身体之轻,纵身一跃,跳出了人群。卡尔维诺选择将诗人的轻盈一跃这一形象作为自己走向新千年的吉祥物。
因此,他说自己的工作常常是要减轻分量——人物的分量、城市的分量、天体的分量以及小说结构与语言的分量。在我看来,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树上的男爵》中主人公的绝妙结局:性格坚定的男爵,在青年时代因为和父亲的冲突而愤然爬到树上,发誓终生不再回到地面。他果然在丛林中度过了几十年。在他生命的尽头,人们好奇事情将如何收场。令人惊讶的是,一只在风中飘摇不定的热气球抛下了锚,寻找着支撑物,奄奄一息的柯希莫突然跳起来抓住绳索,就这样随着气球飘走,消失在了大海的那边。尽管读者知道没有人能够逃脱死亡,但以这种奇特的轻盈方式,作家礼貌地将死神请出了纸页。
这一幕,与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为雷麦黛丝安排的归宿高度合拍:在一阵神秘的风中,俏姑娘被床单带着飞起,永远消失在了鸟儿也无法抵达的天际。纯洁的少女就这样从凝重、悲怆、孤独的大陆上逃离了。
看来,所谓的“轻”,常常意味着从命运沉重的束缚中逃逸出去时的欣快。
“重量”无疑是虚构性叙事必须处理的问题。当人与世界的关系在故事中被重建,轻与重的动力学永远在或明或暗地发挥着作用。刘慈欣的作品也不例外。尽管他写过完全以“轻”为乐事的“大艺术系列”,不过更令人难忘的是一种轻与重之间的巨大张力,一种强烈体现出个人独创性的、在尺度极端不匹配的事物之间建立联系的惊人能力。一方面,作为阿瑟·克拉克的仰慕者,刘慈欣一再追忆着《2001:太空漫游》曾带给他的灵魂震撼,希望自己也能追随偶像,引领读者去仰望星空,感受宇宙那如水晶般坚硬、纯粹、透明的空灵之美。另一方面,作为一名长年生活在基层的火电厂工程师,他对中国的贫穷和落后有着深刻的体验,明白在这片土地上,“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出出空灵思想与沉重肉身之间量子纠缠式的戏剧。
在《乡村教师》中,罹患绝症的老师在临终之际仍在要求懵懂的孩子们背下他们不能理解的牛顿力学三定律,在这现实主义色彩高度饱和的一幕之后,故事忽然跃向了星际战争:神一般的外星人在清扫战场时鉴定着沿途行星的文明等级,被随机抽作地球样本的孩子们面对一系列测试题时无动于衷,直到正确答出了牛顿定律,才证明了地球值得保存。以这种近乎讽刺的方式,人类躲过了一劫,却无人知晓所有的功劳属于一个在这个星球上最贫瘠的角落里默默死去的中国教师。在《中国太阳》里,水娃从赤贫的故乡走向大城市,从摩天大楼外的“蜘蛛人”变成“人造太阳”上的镜面清洁员,最终,与霍金的对话激发了他对宇宙的向往。个体的思想蜕变,寓意着古老农耕民族的觉醒,也隐伏着“轻”与“重”之间的对立统一。最感人的一幕,是太空中俯瞰着地球的水娃,看见一股寒流正在向家乡涌去,在电话中嘱咐爹娘多穿衣服。在无重力的太空与凝重的亚洲大陆之间,轻盈的电波传递着赤子之情。水娃日益开阔、灵动、飘逸的意识,终将引领他失重的身体踏上一去不返的星空深处,同时又超越时空的限制永远牵系着被地心和命运的引力束缚在黄土地上的父母。在这些叙事中,最卑小的个体与最壮阔的时空联结在了一起,人类的情感在冰冷的宇宙中释放了微渺却不可忽略的温度。以这种方式,作家演绎了自己的动力学方程。

最能体现刘慈欣对“重量”感受的,莫过于《流浪地球》。
本来,太阳演变为红巨星尚需几十亿年。我们多少会觉得,那时即便还有人类,也会发展出与这一时间尺度、事件规模相匹配的高超技术。但小说家让灾难突然降临,用可理解范围内的技术构想与社会形态,去承受空前的压力。任务的艰巨与手段的粗陋,形成了极端的不匹配,也由此促成了小说史上最悚然也最迷人的时刻之一:人类为地球装配上巨型发动机,推动着母星逃离太阳系。
尽管地球赋予了我们对诸多事物的重量感,但当它被想象成无尽星海中的一颗小小行星时,自身却缺少重量感。正是安置在亚洲和美洲大陆的一万两千台行星发动机,让母星59万亿亿吨的质量有了可感性。在漫长的旅途中,地球将不断地燃烧自身的一部分来为其余的部分提供动力,实实在在地做着卡尔维诺所说的“减轻星体重量”的工作,却因此令星体的沉重感愈发凸显。据说,好莱坞的技术团队听到这个故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疑问就是:为什么不逃离地球,而要拖着它离开太阳系?鲜明的重量感显然能瞬间楔入读者的意识深处。
巨大的重量必然导致自我碾压。作为概念惊人的短篇小说,《流浪地球》最主要的看点是地球“刹车时代”与“逃逸时代”文明的凋敝:滔天巨浪漫过城市的废墟,洪水退潮时从摩天大楼的残骸中倾斜而下的道道瀑布,穿越小行星带时流星不断撞击造成的漫天尘埃经年不散……其中最恐怖的,当属地球与木星会合时地平线上缓缓升起的红色天幕:
这个在木星表面维持了几十万年的大旋涡大得可以吞下整整三个地球。这时木星已占满了整个天空,地球仿佛是浮在木星沸腾的暗红色云海上的一只气球!而木星的大红斑就处在天空正中,如一只红色的巨眼盯着我们的世界,大地笼罩在它那阴森的红光中……
而这只是将持续两千五百年的漫长苦难的开始,是一百代人类将要经历的连番劫难的序章。显然,这个关于“逃逸”的故事以不断“叠印”沉重感为乐事。和诗人圭多·卡瓦尔坎蒂的轻盈一跃不同,刘慈欣说,在为命运一点点加速直到它逃出死亡的引力前,我们必先付出沉重的代价。
然而,在灾变的一次次淘洗中和重量感的一次次冲压下,仍然有事物存留下来并变得愈发密实:比珠峰还高的行星发动机、能容纳百万人口的地下城、太空舰队为清扫小行星障碍而发出的反物质炸弹……面对恒星之死,如细菌般渺小的人类制造出来的这些事物,显得笨拙、粗陋,勉强维持着文明的苟延残喘。换言之,当文明的容颜枯萎、血肉成尘,重工业的铮铮骨架就将在冰雪茫茫的大地上显露,以自身的笨重烘衬着“流浪地球”的滞重,同时,又与这种滞重构成了对抗,呈现出一种微末之物的“顽固”性,这是那种被美杜莎的目光石化后的粗粝感,却以其抗压性支撑着人类最后的生存空间。这一点,在电影中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和丰富的呈现:民俗风味浓厚的地下城、轮胎比人还高的巨型运载车、原作中不存在的领航员号空间站等等,这些事物,凝聚着一个物种不屈的抗争精神,也在某种程度上“坐实”了刘慈欣的“工业党”身份。
关于现代科学与工业文明的利弊,人们各有高见。在刘慈欣看来,人类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发展科学技术、提升工业水平,唯有如此,才能在未来的种种天灾中赢取生机。对这一点,他从未有过质疑。不管人们对此如何誉毁,这里只想说,刘慈欣作品的钢铁底色其来有自。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拖入了西方主导的民族大竞争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渐成公理。连番的挫败催生了文化革新的诉求,国人对科幻小说的兴趣也从此而来。光绪二十八年,梁启超树起“小说界革命”的大旗,主张通过小说改造民众,包括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在内的科幻小说成为备受青睐的类型之一。光绪二十九年,23岁的周树人为他的科幻译作《月界旅行》写下一篇序言:作为一种渴望不断进步的生物,人类通过不懈的奋进,努力摆脱着自然的奴役,逐步走向更高的自由,《月界旅行》正是“以其尚武之精神,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人历经磨难才赢回世界的几分尊重,中国科幻也几经沉浮才终于在新千年里结出硕果。当对怪力乱神无感的理论家们寻找着能让人类彼此和谐共处的新思想时,来自山西娘子关的工程师刘慈欣却只想提醒:思考一下灭顶之灾降临时人类该如何逃生吧!这种对生存的焦虑、对进化的执着以及对科学的崇拜,正是近现代中国核心命题在星际尺度上的再表达。
表达的结果经常显得简单粗暴。许多人说,不管刘慈欣的想象力如何,他的语言还是太差了。确实,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人物塑造、情感深度发掘等方面,刘慈欣的问题显而易见。但是,如果把作家的“语言”能力理解为准确、有效地用文字来言说他对世界的思考、想象和情感,那么,在由远古的神话、庄子的寓言、屈原的赋、李白的诗、东坡的词……所构建的华夏文学长河中,伟大而浪漫的心灵虽然一次次奏响过生命的律动,创造了众多不朽的篇章,但如何用汉语去表现科学革命之后的时空之广袤、探索之艰辛、定律之奥妙、技术之恢弘,抒发现代中国人的豪迈和悲悯,则是一个多世纪前才出现的全新任务。刘慈欣的写作,正代表了中国作家在尝试承担这一使命时的某种可能性。在这个充满挫折和挑战的过程中,他至少为汉语文学贡献了生猛、奇崛、壮阔的意象,勇毅、果决、进取的气质,崇高、悲怆、庄重的语调,而所有这些共同塑造了他的文学语言质地。
就《流浪地球》而言,“地球流浪”这个光芒四射的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惊人的重量感,是小说最核心的魅力之源,而人类依靠残损的工业体系对这沉重的压迫所做的壮烈抗争,则是情感共鸣的关键触发。对我这样的读者而言,有这两点,已然足够。令人欣慰的是,电影虽然对原著做了相当大的改造,但两个关键点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事实上,从小说到电影的媒介转化过程,正好表明了大刘作为一个科幻艺术家的才华过人之处究竟何在)。如果说我对大银幕上的《流浪地球》还有什么不满,那也与技术设定是否无懈可击、情节安排是否合理、人物塑造是否成功、特效是否出色、剪辑是否流畅、价值观是否荒谬等等毫无关系。让我感到最不过瘾的,是地球在无际长夜中默默前行的镜头太短。如果可以,我想久久地凝视这小小的蔚蓝色行星,看着它在千万簇幽微火焰的推动下,迟缓而坚定地告别故乡。
是的,太阳完了,太阳系完了,可是,地球还没完。我们要用笨重可笑、破破烂烂的设备,拖拽着遍体鳞伤的母星,逃向新的家园。请不要问为什么,这就是我生存意志的最后表达。(图片来自网络)
本文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凤凰网读书”,内容有所删减,此处为未删减版,经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贾立元副教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