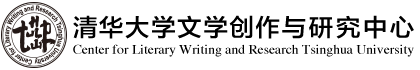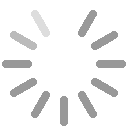本文原载《国际儒学》2022年第2期,原题《反复论辩的“重言”及其他——儒道会通视野下的<庄子>校读三题》
反复论辩的“重言”及其他
——《庄子》校读三题
解志熙
提 要:由于《庄子》的不羁之思和奇妙文体,加上历代的传抄、刻本亦不免讹误和异文,所以《庄子》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语文问题。如历来训诂对《知北游》中“汝唯莫必,无乎逃物”等句有误解,而《田子方》、《庚桑楚》两篇或许也暗藏着文字讹误问题。文章进而纠正了历来对《寓言》篇所谓“重言”的误断和误解,或者有助于重新认识《庄子》的写作过程和思想进路。
关键词:《庄子》 重言 反复论辩 写作过程 思想进路
《庄子》以奇妙之词言说玄妙之道,开创了中国“诗化哲学”之先河,所以深得历代道流文士之喜爱。可对我这样一个朴鲁之人,庄子哲学就显然华而不实、碍难肯认了。不过,我仍然喜欢读《庄子》,但我的阅读只是想仔细看看庄子天花乱坠、喋喋不休的说辞,究竟在语文学上是什么意思。这样一种阅读趣味自然不很高上,但也不失为有趣的消遣吧。就是怀着这种不甚高上的阅读动机,几年来锱铢必较地读完了历代比较重要的《庄子》校注本——从郭象的《庄子注》、成玄英的《庄子疏》(郭注之疏)和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庄子音义》、林希逸的《庄子鬳斋口义》、焦竑的《庄子翼》、宣颖的《南华经解》,直到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及刘武的《庄子集解内篇补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刘文典的《庄子补正》、王叔岷的《庄子校诠》等。这些注本都遵循着中国文献学的优良传统,近人注本则于文献学之外也兼用西方的语文学方法,其认真的校释很有助于读者理解《庄子》的文义。当然,由于《庄子》的奇妙文体和不羁之思,有些文句实在不易理解,加上历代的传抄、刻本亦不免讹误和异文,所以这些校注著作也没有完全解决《庄子》的语文问题,可能还存在着一些误断和误解之处。这里就从自己的阅读手记中摘出几条,聊为举隅之谈吧。为方便起见,下引郭象《庄子注》、成玄英《庄子疏》(郭注之疏)和陆德明《经典释文》等古训,均据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所引,不再一一说明。说来可笑的是,由于自己是逐字逐句地反复阅读和校读的,这使我对《庄子》之不厌其烦、反复论辩的文体特点及其在不断重复中逐渐曼衍的思想进路,实在印象深刻,终于有点明白《寓言》篇里所谓“重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可能是《庄子》研究里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这里就先从《知北游》、《田子方》、《庚桑楚》篇几处文句的校读意见说起,然后再略说对《寓言》篇所谓“重言”问题的看法。
一、玄思的话语套路:
《知北游》中的“汝唯莫必,无乎逃物”问题
《知北游》中有一段东郭子与庄子的问答,是颇富玄思的段落,历来的注解几乎一以贯之。这段话并无文字讹误或句读误断问题,兹据郭庆藩《庄子集释》标点本引录如下——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1]
这段话里既有“道”又有“无”,于是以“无”释“道”就成了历来的主导性解释。如郭象在关键句“汝唯莫必,无乎逃物”后施注云:“若必谓无之逃物,则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则未足以为道。”[2]郭象之所以说“必谓无之逃物,则道不周矣”,就因为他以“无”为“道”之本,故“无”逃于物,则“道”就不周——缺乏普遍性,也就不足为“道”了。成玄英于“庄子曰:‘在蝼蚁’……东郭子不应”一长句后,也加疏予以补充:“大道无不在,而所在皆无,故处处有之,不简秽贱。东郭未达斯趣,谓道卓尔清高,在瓦甓已嫌卑甚,又闻屎溺,故瞋而不应也。”[3]而在“汝唯莫必,无乎逃物”句郭象注后,成玄英之疏又进一步发挥道:“无者,无为道也。夫大道旷荡,无不制围。汝唯莫言至道逃弃于物也。必其逃物,何为周徧乎?”[4]并在“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句的郭象注“明道不逃于物”后,又加疏强调说:“至道,理也。大言,教也。理既不逃于物,教亦普徧无偏也。”[5]王先谦的《庄子集解》认同郭象注和成玄英疏,只在“汝唯莫必,无乎逃物”句后加了一个补注以示强调云:“言汝莫期必道在何处,无乎逃于物之外也。”[6]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是《庄子》注疏的集大成之作,但于此段也只增补了一些字词的训诂,大意仍不出郭象注和成玄英疏。直至刘文典的《庄子补正》于此段的解释仍全袭郭象注和成玄英疏,而别无发挥。总而言之,从郭象到刘文典的历代注疏,大都以无为道之本而一致强调道无所不在、处处有之、故无逃于物、普遍无偏也。
这个一以贯之的解释,似乎误解了《知北游》里这段话的玄学论辩之本义。诚然,《庄子》在本体论(存在论)上确实上承老子,有所谓有无本末之论,声言“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秋水》),“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庚桑楚》)等等,且以为“无”是第一位的,“有”是第二位的。从这种本体论又派生出“虚静”“虚无”“无为”的人生观,成为《庄子》哲学之常谈。《庄子》哲学的这种崇无倾向恰与魏晋时期开始流行的佛学“性空”观念相合,所以自此以后的《庄子》注疏就特别地强化了这一点,这便是上述郭象注等对《知北游》此段话的误解之由来。之所以说是“误解”,是因为《知北游》的这段话实际上并未涉及“无”的问题,所以用“无”的思想来统摄整个阐释,既不符合这一段话的思想条理,也不符合这一段话的语言修辞。

(“道在瓦甓”书法作品)
历来的注家似乎都未注意到《知北游》这段对话的话题,乃是导源于老子《道德经》的著名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按照老子的观点,“道”作为世界的最高的本体或本源,是不可道、不可名的,凡可名、可道者都不是“常道”。庄子是老子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挥者,他在《知北游》此段里接着老子的话题,设想出“东郭子”与庄子自己的论辩,进一步发挥了老子的玄学思想。庄子的论辩分为两个层次。在第一个层次,针对东郭子“所谓道,恶乎在”的问题,庄子的回答是道“无所不在。”这是老子的原话里隐含而未发的意思——作为宇宙之“常道”或“至道”,道是无所不在、普遍呈现的,所以不择高下,当然也“在稊稗”以至“在屎溺。”可是话说到如此“每下愈况”的地步,东郭子显然有点接受不了。对东郭子的疑惑与抗拒,成玄英的疏至少有一点是揭示得不错的:“大道无不在,……故处处有之,不简秽贱。东郭未达斯趣,谓道卓尔清高,在瓦甓已嫌卑甚,又闻屎溺,故瞋而不应也。”于是有了庄子的第二层论辩。在此,庄子着重指出了东郭子问道之“期而后可”的思想方法问题:“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汝唯莫必,无乎逃物。”关于东郭子问道的“期而后可”之迷思,郭象注谓是“欲令庄子指名所在”,这是准确的语文解释。但包括郭象在内的诸家注解,都没有看出东郭子问道的“期而后可”之迷思,正是犯了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指斥的以偏概全之弊,也没有看出东郭子的思想方法正是孔子所批评的“固”“必”之病——东郭子的“期而后可”乃正是“固”“必”的表现。这或许因为在郭象、王先谦、郭庆藩以至于今人刘文典、王叔岷等《庄子》注家眼中,孔门乃是庄子的最大论敌,所以他们也就以为庄子不会吸取孔子的思想和语言。于是他们对庄子批评东郭子思想方法的话——“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汝唯莫必,无乎逃物”——之解释,也就完全撇开了显而易见的孔子思想与语言的影响,把这几句并不难懂的话解释得很牵强。即如博雅多闻、治学严谨的王叔岷对“汝唯莫必”之解读,就无视孔门的相关言论,而别出新解云:“莫犹无也。古音无如莫。……‘唯莫’与‘唯无’同。此谓‘汝唯莫必,必则无乎逃物’也。必,犹今语‘肯定’。” [7]如此一来,本是庄子批评东郭子的话,竟成了庄子的肯定之论,这就与庄子的原意大异其趣了。王叔岷甚至据此把《知北游》正文径改为“汝唯无必,无乎逃物”。如此改字、添字以求解,就走到严谨的反面,而不足为训了。
其实,正因为孔门乃是庄子的最大论敌,所以庄子对孔门的思想和言论是下了功夫的,因而是很熟悉的,在《庄子》中涉及孔门师弟的论辩不下百处,的确是牵涉最多的前辈思想家。其中,既有对孔门师弟的许多批驳以至丑化,也有对孔门的思想和言论之汲取——这两方面都是存在的。这种矛盾的互文关系是不应忽视的。即如《知北游》此段中的“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汝唯莫必,无乎逃物”二句,就显然借用了《论语》里的“子绝四,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以及“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以批评东郭子的思想方法之偏颇,正犯了孔子所谓“固”“必”之病。并且,“汝唯莫必”一句里的“莫”字,也正如《论语•里仁》篇里的“无莫也”之“莫”一样训为“慕”。[8]可历代学者似乎都没有注意到,《知北游》里的“汝唯莫必”与《里仁》的“无莫也”之两“莫”字同训。至于“必”字,朱子《论语集注》即于“毋必”句下加注云:“必,期必也。”[9]而在《知北游》里庄子批评东郭子“汝唯莫必”,指的正是前边东郭子问道之“期而后可”的要求。这在《庄子》里还有同样的用例,如“外物不可必”(《庄子·外物》)等。要之,在庄子看来,东郭子“期而后可”之问“道”,欲指名道之所在,正是孔子所谓思想方法上的“固”“必”之病,因为“道”恰如老子《道德经》所强调的那样,是无所不在而又无可称名的至高本体,一旦把“道”指实为某事某物,那就把“道”局限于具体事物,而使道失去“周徧咸”的普遍性,因而也就不成其为“道”了。此即“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这关键一句的意思。倘若把此句用今天的白话来疏解一下,那意思就是:正因为你(东郭子)一心期望着把“道”指实为必是某事某物,那将不可避免地使“道”局限于某物,而不再是具有最大普遍性的无所不在的“道”了。反观自郭象到王叔岷的注解,几乎一致地把“无乎逃物”解为“至道无逃于物”且以此为“道”的普遍性之所在,并视“至道无逃于物”为庄子的正面意见。这与《庄子》的本义完全相悖了。那原因就在于他们没弄明白从老子到庄子的思想条理和话语套路——正因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以好“道”之人就绝不能“固、必、慕”以求“道”,否则,“汝唯莫(慕)必”一定会堕入“无乎逃物”的陷阱。

(庄子画像)
扩大一点看,《知北游》里的这段玄谈论辨其实是古今中外形上学玄思话语的典型套路,尤其成为那些狡黠的思想家或哲学家“王顾左而言他”的思想狡计。认真的思想家、哲学家面对这个“第一义”的本体论之难题,他们在执著的探求之后,总会尽可能地给出答案,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叔本华的“意志”、马克思的“物质”是也,然而他们如此说定了也就因此说死了,必定会遭到这样那样的质疑而难以自圆其说。此所以狡黠的玄学思想家、哲学家总会给自己预留金蝉脱壳之计:一方面,他们会宣称第一义的本体无所不在、呈现在万事万物中,另一方面,面对究竟什么是第一义的本体之追问,他们一定会“王顾左右而言他”,声称第一义的本体是不能指实的、不可名状的,凡可指实者、可名状者只是某物而已,普遍性的本体是不能被物化的。在中国,这种“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话头,是禅宗高僧的遁逃妙计而屡试不爽。《五灯会元》所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之问答就有三百多条,都是问本答末、答非所问的套子。如卷二“天柱崇慧禅师”条:“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白猿抱子来青嶂,蜂蝶衔花绿蕊间。’”[10]如卷九“韶州灵瑞和尚”条:“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十万八千里。’”[11]再如《祖堂集》卷十八记著名的赵州和尚与僧人的问答:“(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亭前柏树子。’”[12]有的禅宗高僧如云门禅师对“如何是佛”这样的根本问题,竟然以“干屎橛”相答。[13]诸如此类的问答,与上述《知北游》里的玄学论辩颇为相似,都因所问涉及“第一义”的本体问题,问者本不应固必以求——“汝唯莫必,无乎逃物”,答者自然是规避为妙,也就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以免着了迹象、落了言诠。这种玄思问答话术演变到后来,便成了狡黠地答非所问、让对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思想游戏。禅宗所谓“话头禅”即是典型例句。在西方,如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就认为有所谓先于、优于一切存在者之存在,它是一切存在者的基础和本源,所以他称之为“基础本体论”(Fundameutalontologie),并强调作为基础本体的存在既不是时空中的“事实”(客体),也不是超时空的“自我”(主体),故此科学和理性都不可能认识它、概括它,而只能通过人这种存在者显示其意义。于是海德格尔的哲学便成了对这个神秘的存在本体之无限曼衍的思辨追寻游戏——他总是引领着听者和读者兴头头地去追寻那个存在的真身,眼看要追寻到了,海德格尔却说,咳,这只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还不是那个存在的本体啊,不过海德格尔会鼓励听者和读者说,另外还有线索可以继续追问啊,于是听者和读者又随着他继续追问,然后,当然又是同样的失落、而又得到继续的鼓励,如此无限曼衍下去,听者和读者陷溺在这个永远也追寻不到存在真身的追寻过程中。这其实是海德格尔这类形上学家预设的思想-话语套路:他向你保证有所谓存在的真身,但又强调说这个存在的真身不是事实性的存在、不是物化的东西,所以不可认识、不可概括,一如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或庄子所谓道“无所不在”但不可“固必”以求,“汝唯莫(慕)必,无乎逃物。”狡黠的哲学家都擅长以如此这般的思想圈套让读者陷溺其中,他自己则早已预留了金蝉脱壳之计。古今中外喜欢玩这套思想游戏的大有人在,读者初次看到,无不惊讶其奇妙,看得多了,亦不难猜出那玄学闷葫芦里早就预装了逃遁的思想—话语狡计,也就索然寡味了。当然,也有人被诱入这套思辨游戏里终生走不出来,津津乐道焉、苦苦思索之,成了玄思的俘虏。二、并非偶然的巧合:
《田子方》中的“慹”与《庚桑楚》中的“熟”之臆测
说来有趣,《庄子》笔下的老子似乎是一个很讲究卫生的人,尤其喜欢濯发、沐浴,《田子方》篇里就有一段话讲到老子的“新沐”——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见,曰……。据说斋戒之礼始于殷商,至西周已成定制。而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曾任“周守藏室之史”,[14]大概也因此得以分享沐浴斋戒之礼,到后来老子隐居宋国沛地,仍保持了爱洗头、沐浴的习惯,成为其养生的享受之一。孔子的拜访老子,恐怕还是老子担任“周守藏室之史”的时候吧。其时风尘仆仆的孔子来造访老子,正赶上“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慹然似非人。”按,“沐”的本义是“濯发”,广义上则可说是洗涤以至洗澡,这里就且算是老子在“濯发”吧。至于描写老子新沐后情状的“慹”字,古典训诂学家的注疏比较简单。郭象注谓:“寂泊之至。”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引卢文弨之说:“慹,乃牒反,又丁立反。司马云:不动貌。《说文》云:怖也。”[15]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和刘文典的《庄子补正》也都是抄录旧注,没有进一步的解释。王叔岷的《庄子校诠》略有辨析,也只是肯定了《庄子集释》所引“司马云:不动貌”的解释。总之,古训不外两义:一是寂然不动貌,一是可怖的样子。说一个人新沐后寂然不动,已勉强为训了,至于《说文》所云“怖”,实在与新沐乎的情景太不相侔,所以不为历来注家所取。看得出来,古今注家比较一致地肯认“慹”是“不动貌”,可是一个人新沐后就“不动”了,这有什么好说的?而“慹然”与“似非人”又如何通释?并且“慹然似非人”又何以成为老子不便见孔子的原因?诸如此类的问题表明,用“不动”释“慹”并不是很妥帖,甚且让人怀疑“慹”字是不是用错了?无独有偶,《庚桑楚》篇有一段南荣趎与老子的对话,这一次老子说到了“洒濯”——南荣趎请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恶,十日自愁,复见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熟哉郁郁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犹有恶也。……”这段话并不难懂,所以郭象无注,成玄英则疏解前五句云:“(南荣趎)既失所问,情识芒然,于是退就家中,思惟旬日,征求所好之道德,除遣所恶之仁义,未能契道,是以悲愁。庶其请益,仍见老子。”又疏解后三句云:“(南荣趎)归家一旬,遣除五德,涤荡秽累精熟,以吾观汝气,郁郁乎平,虽复加功,津津尚漏,以此而验,恶犹未尽也。”按照道家的观点,儒家所推崇的仁义不仅无助于人类,反倒是误人之恶,所以是应该涤除的。就此而言,成玄英的疏解是不错的。只是他对此段对话中的“熟”字之疏解,似乎不很妥帖。因为《庚桑楚》里老子的话,显然是以人日常讲究卫生的“洒濯”作为涤除“仁义”之恶的比喻,并且从其上下文中可以看出,其所谓“洒濯”不是一般的洗头洗脸之类,而应当是热气腾腾的洗个热澡,以涤荡全身秽累,可成玄英之疏却将“熟”解读为“涤荡秽累精熟”而又谓“恶犹未尽也”。这就有点讲不通了——如其“涤荡秽累精熟”,又怎会“恶犹未尽也”?换言之,如其“恶犹未尽也”,就不能说“涤荡秽累精熟”了。这让我怀疑“熟”未必是“精熟”之意、甚至怀疑“熟”不当作“熟”,而应该是另一个字也未可知,作“熟”乃是误抄误刻吧?两处情景和用字如此相似恐怕并非偶然,则《庄子》这两段对话里的“慹”“熟”会不会是同一个字?如果是,又该是哪个字?这让我想起自己的训诂学启蒙老师彭铎先生的教诲。彭铎先生(1913—1985),湖南湘潭人,毕业于中央大学,乃是著名学者黄侃的弟子。彭先生专治文献训诂之学,精熟先秦汉魏典籍,上世纪五十年代支援西北,来到西北师范学院任教。1978年春我考入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当时的系主任就是彭先生。1979年彭先生为我们开设了训诂学的课程,发的铅印讲义即今整理出版的《文言文校读》。在这门课程和讲义中,彭先生针对我们这些年轻学子读古书难的问题,精心选择了先秦两汉文献中记述同一事件的各种文本,进行比较对勘,指示给我们一种阅读、理解古书的方法。即如初看古书的人掌握词义是个难关,而词义往往可以通过比较对勘去了解,其例如关于“邵公谏厉王弭谤”的记载,《国语•周语》中有句云:“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这两句话中的“为”字究竟该怎样解释?参照《吕氏春秋•达都》中的相关记载——“是故治川者,决之使导;治民者,宣之使言”,则《国语•周语》中两“为”字之意义便涣然冰释。[16]彭先生开示的这种方法显然继承了汉学家校理文献的方法,难得的是,彭先生并不泥守汉学家法和文献学的范围,而有意推而广之,使之成为一种超越了文献校释的读书方法,以至于一种“通过参校材料,对比地去分析问题”的治学方法论。[17]我得老实承认,彭先生的校读示例给我很大的启发,觉得对《田子方》里的“慹”字,也不妨参照《庚桑楚》中近似的“熟”字来校读一下。下面删繁就简,只举句子主干——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田子方》)老子曰:“汝自洒濯,熟哉郁郁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犹有恶也。”(《庚桑楚》)看得出来,不论是“慹然”之“慹”还是“熟哉”之“熟”,都是形容人新沐后尚未干净整齐时的情状,所以窃以为在《庄子》的原初文本里,这两个字很可能是同一个字,而且这两个字的字形也确实很近似啊,只是郭象作注之时所据抄本就可能出现了误抄。因此,也就要追问一下:那正确的“同一个字”究竟应该是“慹”字还是“熟”字呢?这又让人左右为难了——因为“慹”字的意思太抽象、太装模作样,很不“自然”;“熟”字则根本不合人新沐后的情状。那么,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不论《田子方》里的“慹”字还是《庚桑楚》中的“熟”字,其实都是那“同一个字”之误写?或许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当然,如果要尝试从这两个误写中校读出那原本正确的“同一个字”,则那原本正确的“同一个字”,既必须合乎人新沐后之情状,又必须与“慹”字和“熟”字很相似。然则,那原本正确的同一个字,究竟是个什么字呢?窃以为,那很可能是“热”字。一则不论从篆书、隶书来看,“热”字都与“慹”字和“熟”字很相似,二则“热”字也恰合这两段话里所写人新沐后的具体情状。这里,就且用“热”字替代那两句话里的“慹”字和“熟”字——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热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老子曰:“汝自洒濯,热哉郁郁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犹有恶也。”显然,“热”才是人新沐后的典型情状,所以把“慹”字和“熟”字校改为“热”字后,这两句话就不再费解了。只是上段话里的“热然似非人”还嫌描述简略、不很具体,而参照下段话里的“热哉郁郁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犹有恶也”,就很容易理解“热然似非人”的老子为什么不能立即见孔子了,因为他新沐后闷热郁郁、热汗淋漓、披头散发,自然不是一个上流人士在正常情况下应有的人样子,怎么好见客呢?所以也就只能让“孔子便而待之”了。顺便说一下,在先秦典籍里,“洒濯”或“沐浴”似乎与“热”是相伴相随的搭配。比如《诗·大雅·桑柔》就有句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孟子·离娄上》亦云:“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这些早于或近于《庄子》的用例,或者可以作为《庄子》里“慹”与“熟”当为“热”之旁证吧。
三、由来已久的误解:
《寓言》篇所谓“重言”究竟是什么意思?
《寓言》篇虽然列在“杂篇”,但它说明了《庄子》的语言修辞特点以至思想表达特点,带有自我总结之意,近似全书的自序,所以还是很重要的。而最重要的自然是开篇那一段提纲挈领的话,由于诸本断句标点无异,这里就据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点校本引录如下——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之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这段话揭示了《庄子》的三个语言修辞特点“寓言”“重言”“卮言”,并对这三个特点作了扼要的解释。由于《寓言》篇自身的解释也近乎“寓言”(如“亲父不为其子媒”)且夹带着“玄言”(如“天倪”),所以自郭象以来诸家对“寓言”“重言”“卮言”不能不作再解释,而大都一依《寓言》篇自有的解释来加以进一步的说明,口径颇一致、很少歧义的。关于“寓言”,郭象注云:“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成玄英疏云:“寓,寄也。世人愚迷,妄为猜忌,闻道己说,则起嫌疑,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信九矣。故鸿蒙、云将、肩吾、连叔之类,皆寓言耳。”陆德明《经典释文》云:“‘寓言十九’,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也。”[18]明末清初人宣颖的《南华经解》云:“寄寓之言,十居其九。”[19]这是对此前注疏所谓“十言而九见信”的纠正。近世注家王先谦、王叔岷等接受了这个纠正意见,至其对“寓言”本身的解释,则与郭注、成疏、陆德明《经典释文》无异。关于“重言”,郭象注云:“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郭象并在“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句后加注强调说:“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虽使言不借外,犹十信其七。”这就为“重言”的解释定下了调子。成玄英疏就接着郭象注进一步说明道:“重言,长老乡间尊重者也。老人之言,犹十信其七也。”这就是说,“重言”即是耆艾长老之言,所以为人信重也。到了陆德明《经典释文》,就将郭注、成疏确定为一句话:“‘重言’谓为人所重者之言也。”[20]宣颖的《南华经解》更其扼要地总结说:“重言十七”乃是“引重之言,十居其七”之意。[21]王先谦的《庄子集解》援引宣颖的断言后,又引姚鼐的话作为进一步的解释:“庄生书,凡托为人言者,十有其九。就寓言中,其托为神农、黄帝、尧、舜、孔、颜之类,言足为世重者,又十有其七。”[22]这显然是把“寓言”与“重言”打通了解释的。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引郭注、成疏、陆德明《经典释文》,别无补充。王叔岷的《庄子校诠》赞同上述解释,并加按语强调说:“案重言者,借重人物以明事理之言也。《淮南子•修务篇》:‘世俗之人多尊古而卑今,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所谓托古是也。”[23]只有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引其大伯父郭嵩焘的话说——“家世父曰:重,当为直容切。《广韵》:‘重,复也。’庄生之文,注焉而不穷,引焉而不竭者是也。郭(指郭象)云‘世之所重’,作柱用切者,误。”[24]按,柱用切之“重”读zhòng,厚重的意思;直容切之“重”读chóng,复叠的意思。郭庆藩并在“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几句后又附加郭嵩焘的通释云——“家世父曰:已言者,已前言之而复言也。《尔雅释诂》:耆艾,长也。艾,历也。郭璞注:长者多更历。《释名》:六十曰耆;耆,指也,指事使人也。是耆艾而先人之义。经纬本末,所以先人,人亦以是期之。重言之不倦,提撕警惕,人道如是乎存。”[25]郭氏的意见是一个很重要的补正,可惜一直没有引起其他学人的注意。至于“卮言”,郭象注云:“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唯彼之从,故曰日出。日出,谓日新也。日新则尽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尽则和也。”成玄英疏云:“卮,酒器也。日出,犹日新也。天倪,自然之分也。和,合也。夫卮满则倾,卮空则仰,空满任物,倾仰随人。无心之言,即卮言也,是以不言,言而无系倾仰,乃合于自然之分也。又解:卮,支也。支离其言,言无的当,故谓之卮言耳。”陆德明《经典释文》则补充说:“‘卮言’字又作‘巵’,音支。《字略》云:巵,圆酒器也。李起宜反。王云:夫巵器,满即倾,空则仰,随物而变,非执一守故者也;施之于言,而随人从便,己无常主者也。司马云:谓支离无首尾言也。”卢文弨又辩证说:“卮旧作巵,……今多省作卮。”[26]看得出来,以上历代注家对“寓言”“重言”“卮言”的解释,其实分歧不大。关于“寓言”,诸家几乎没有分歧,所以此处不论。关于“卮言”,诸家略有分歧,分歧则源于《寓言》篇本身说“卮言”时用酒器“卮”做比方,这就不免导致理解上的分歧。不过分歧也不大——概言之,庄子所谓“卮言”,不过是说自己作文发抒思想,乃是像饮酒一样随兴倾洒、随意而为的随笔,如此与时俯仰、随时曼衍,所以不很严谨吧。关于“重言”之训解也基本上一致,多数注家都强调“重言”乃是援引足为世重的前辈人物之言以强化自己的观点。只有郭庆藩引郭嵩焘的话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那是很重要的补正,但郭氏的意见显然未受重视。应该说,《寓言》篇所谓“重言”是一个既简单又重要的问题。说它简单,是因为《寓言》篇原文已说得明明白白——“重言”即“所以已言也是为”,也即郭嵩焘所谓“已前言之而复言也”,可是主流的注疏却把它解释为“引重之言”云云,非常曲折缠绕,反而不得要领、滋生了误解;说它重要,则不仅因为“重言”涉及整个《庄子》的语言修辞特点问题,而且涉及庄子的思想进路、思想特点问题,以至于整部《庄子》的写作过程、文本构成和作者归属等重要问题都与此相关。所以对“重言”的理解,的确关系甚大,不能不有所辨析也。 三十年前我最初通读《庄子》,读的就是王先谦的《庄子集解》本——此书编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比较容易到手,所以购来闲时翻阅。记得读到《寓言》篇的“寓言”“卮言”之解诂,觉得都还通达,可以接受。可是王先谦对“重言”的解释,只引宣颖所谓“引重之言”,我觉得这与《寓言》篇自身的解释“所以已言也”,实在对不上号。其实《庄子》为文常说半句话,省去的就让读者去脑补,“所以已言也”的完整意思并不难补全,那就是“已言而复言之”之意,只是《寓言》篇把“复言”的意思省掉了而已。可是王先谦却把“所以已言也”解释为:“已,止也,止天下淆乱之言。”[27]这就有点刻意求深,把一个简单的词语复杂化了,所以我不大能够接受,也因此就记住了“重言”这个词语。再后来读到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和王叔岷的《庄子校诠》,也是同样的解释,仍然不能说服我。并且由于刘、王之著比较完整地引录了郭象注、成玄英疏和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由此我才发现所谓“引重之言”的解释来头甚早,王先谦、刘文典和王叔岷等大概也是遵循“疏不破注”的训诂学传统吧,所以他们只能沿着这个方向解释得越来越详密,人们也就不敢怀疑了。好在我不是专门研究古典的学者,不大迷信古训,也就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怀疑。直至读到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所附郭嵩焘的说法,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很佩服郭氏治学的实事求是。不过,郭氏毕竟是给《庄子》做注疏而非写论文,难以申论其理据,并且郭氏也与其他人一样,以“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绝句,这同样误断了句子、误解了《寓言》篇所说“耆艾”几句的意思。下面就不揣谫陋,略说个人对“重言”问题的一点意见。按说,《寓言》篇对“重言”的直接解释“所以已言也”并不难解,不就是郭嵩焘所谓“已前言之而复言也”的意思吗?可是为什么从郭象到王叔岷这些博学的古今训诂学家却要将它曲折地解为“引重耆艾之言”的意思呢?这是我多年深感纳闷的疑问。直到近年反复寻绎《寓言》篇此句的上下文,仔细比勘诸本的句读或标点,才发现历来注家都把《寓言》篇关于“重言”的几句话误断了两句——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这个古今一以贯之的句读或断句,在“所以已言也”处点断,将“是为”与“耆艾”连读,于是下面关于“耆艾”的几句话,也就成了对“重言”的正解:按照中国人的敬老传统,惟其是“耆艾”,所以“耆艾”之言也就必然被人“引重”了。这就是“引重耆艾之言”说的来历。其实,这种断句和基于这种断句的解释,乃是前人好顺着词气语调点读语句的习惯所造成的一个不易觉察的误断和一个不易发现的误解——人们顺着词气和语调读,很自然地觉得在“所以已言也”处该停顿和点断,接着把“是为”与“耆艾”一气连读,也似乎自然而理顺。可是这样断恰恰错了,而且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导致了历来对“重言”的误解。实际上,《寓言》篇本身对“寓言”和“重言”的解说,用的都是同样的句式、同样的修辞、同样的语义条理。不妨先看《寓言》篇“寓言”的解说,其辞曰:“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之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这里对“寓言”的直接解释,是很简洁的“藉外论之”,然后,庄子又用了一个比方、一段近似“寓言”的话——“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之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来间接地解释“寓言”之“藉外论之”的特点,其意诚如郭象注所说:“父之誉子,诚多不信,……辄以常嫌见疑,故借外论之。”[28]因为父子是血亲,父亲无论如何也会为儿子说好话的,所以他的好话就不大可信,可要是外人说他的儿子好,那就比较客观、比较能取信于人了。显然,父子内外关系只是打个比方来说明“寓言”之“藉外论之”之理,庄子无意、读者也不能把“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之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这几句话,当作对“寓言”意义的直接解释。比如,能从这几句话里抽象出“非父之言”或“非亲人之言”来作为“寓言”的解释吗?当然不能。庄子的这种话语套路,也同样不多不少地出现在《寓言》篇对“重言”的解说里,可是历来的句读或断句却把几句话误断成了:“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如此断句,使得同样打比方的“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几句话,变成了对“重言”的直接说明,于是年长的耆艾之言为人所重,就成了“重言”的意义之所在以至于“定义”之所是,而完全取代了或者说篡改“所以已言也”这个直接解说。弄清了致误之由,则《寓言》篇解说“重言”的几句话,就该像“寓言”那几句话一样,按照同样的话语套路和语义逻辑,把直接解释的话和间接比方的话区别开来、点断开来。下面是纠正后的新断句——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此处重新断为一句的“所以已言也是为”,是古汉语里表示强调的倒装句式,如“唯马首是瞻”之类。《庄子》里近似的话也不少,如“汤之问棘也是已”(《逍遥游》)、“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应帝王》)。然后,正如同“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之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几句是比方解说“寓言”一样,“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几句,也是对“重言”的打比方的解说:一个有阅历的人应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向后辈们言说一些生活经验与教训,且要不断言说、反复言说,成为传说和传统以传诸后世,才算没白活一世,否则再年长,也无足称道,不过是个陈死人而已——这不是翻译,只是略述大意。如此重新断句,“重言”的解释回到“所以已言也是为”,再也无须拉扯什么“借重耆艾人物以明事理之言也”来加重“重言”的份量了。顺便也纠正一下:历来对“重言”的误断所导致的另一个误解,就是把“重言”逐渐混同于“寓言”。应该说,正由于古今训诂家把“重言”误解为“借重人物(耆艾)以明事理之言”,则“重言”就必然与“藉外论之”的“寓言”相近以至相混。可有趣的是,古今训诂家对如此混同“寓言”与“重言”似乎并无什么违和感,倒是不无欣然之感。如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就引姚鼐的话发挥说:“庄生书,凡托为人言者,十有其九。就寓言中,其托为神农、黄帝、尧、舜、孔、颜之类,言足为世重者,又十有其七。”这就把“寓言”与“重言”打通了或者说“混同”了。王叔岷的《庄子校诠》也强调说:“案重言者,借重人物以明事理之言也。《淮南子•修务篇》:‘世俗之人多尊古而卑今,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所谓托古是也。”就这样,所谓“借重人物(耆艾)以明事理之言”的“重言”就与“托为神农、黄帝、尧、舜、孔、颜之类,言足为世重者”的“寓言”,达到了“十有其七”的重合度。古今训诂家可能没有想到,他们的误解所导致的这种重合,几乎取消了“寓言”与“重言”的区别,这肯定不合庄子或《庄子》之本义。说来,《寓言》篇所谓《庄子》为文好“重言”之本义“所以已言也是为”,也即郭嵩焘所解释的“已前言之而复言也”,这也并非《庄子》所独有,其他先秦诸子如《论语》、《孟子》也都不免“重言”的。这一点早就被汉学家、训诂学家发现了。早在东汉末赵岐为《孟子》作注,就发现《孟子》颇多“重言”,如《梁惠王》上篇前后两段话就是显而易见的“重言”,一是孟子对梁惠王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赵岐并准确指出:“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为齐、梁之君各其陈之,当章究义,不嫌其重也。”[29]到宋代,“重言”甚至成了儒家经典童蒙教本的一个很常见的提示标记。宋刊闽刻本何晏《论语集解》,就每于《论语》的重言处,无不夹注标出是重言。如在《学而》篇“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后,即加有“重言巧言令色鲜矣仁二,本篇《阳货》各一”[30]以提示学子。这个重言的标记,未必是何晏《论语集解》原有的,但至迟也应是南宋人翻刻《论语集解》为教本时所加。并且,这个宋刊闽刻本何晏《论语集解》于“重言”之外,还有“重意”的标注。如同样在《学而》篇“巧言令色鲜矣仁”后,又加 “重意《公冶长》‘巧言令色足恭’。”[31]甚至于这个宋刊《论语集注》书名也叫做“《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32]显然,“重意”其实也是“重言”的表现,只是不限于语言修辞层面的完全之“重复”,而扩展到思想义理层面的大意之“重复”耳。总之,这两种“重言”确为为先秦诸子所共有,而尤以《庄子》之“重言”为最甚。《庄子》的“重言”就集中表现在语言修辞和思想义理这两个层面,前者是狭义的“重言”,后者是广义的“重言”。在语言修辞层面上,《庄子》的“重言”比比皆是——诸如关于“道”或“至道”的妙论、关于“真人”“至人”“神人”的高论,关于“逍遥”与“遁隐”的美谈,反复出现在各篇中,而引用或生造的“黄帝、许由”之对话,齧缺、王倪以至于老子、孔子之事迹,这些“藉外论之”的人物、事迹、言论作为话语套术,被《庄子》各篇翻来覆去述说着、别有用心地发挥着。即如许由拒绝黄帝让天下的美谈和孔子被围陈蔡的尴尬,在《庄子》里就被拿来述说发挥了各自不下十多遍,真让人不能不佩服作《庄子》者竟能如此不厌其烦的“重言”个没完没了!如此等等的“重言”,多到数不胜数,无须举例了。再看《庄子》在思想义理层面的“重意”式“重言”,更是翻来覆去、触目皆是、不胜其重,几乎成了《庄子》思想论辩的一个鲜明特色。诸如对“道”或“自然”的本体论(存在论)之论辩,言与不言、知与不知的认识论之难题,材与不材、有用与无用的反复辨析,物之齐与不齐的价值相对论说,以及有无本末、进退得失的辩证观,……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了《庄子》反复论辩的主题,以至于《庄子》全书从逍遥自得、滔滔不绝之雄辩,直说到谨小慎微、全身避害之衰论,还是意犹未尽、喋喋不休、不肯罢休。如此这般,《庄子》全书始终围绕着几个基本的思想主题反复论辩、不断曼衍,怎能不 “重意”而且“重言”呢?正惟如此,我觉得用“反复论辩”来综括解释《庄子》“重言”之意,可能是比较恰当的。不难想象,当庄子或那个写《庄子》的人到了晚年,把历年所写各篇集中重读一遍,聪明绝顶的他自然会发现,自己的一生为文不少而喋喋不休、反复唠叨,实在重复太多了,以至于“重言”显然成了其语言修辞和思想表述之不可否认的突出特征,于是在《寓言》篇里不得不老实招认:“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这话既是坦诚的自我总结,也带有自我解释以至于自我解嘲的意味——就像一个耆艾长老必须述说自己的生活经验、方能被后辈人称道一样,自己也不得不随兴发抒、随时思考、体会自然、曼衍为文、聊以度日、所以穷年。这很让人同情。记得哲学家冯友兰曾说过,“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33]对一个能够写出《庄子》这样独特思想的哲学家来说,不断思考、反复论辩之“重言”便不得不然了。如此这般不断思考、反复论辩的“重言”进程,一方面固然由于著者始终持续思考着一些相近的思想主题,所以重复提出问题以至于重复运用此前的语言修辞如寓言典故之类,也就在所难免了,但另一方面这种持续思考与写作又不同于近人集中时间撰写所谓专著,而是随时随兴地撰写一些“卮言”性的思想随笔,所以在重复中又有所“曼衍”和发展。由此而进,对《庄子》的思想进路、文本构成以至于作者归属问题,似乎可以有一点新的理解。按,据《汉书•艺文志》,《庄子》原有五十二篇,晋郭象以为其中十九篇为后人所羼入者而汰除之,留三十三篇、编为内外杂篇并为之作注,从此流行,成为今本《庄子》之祖。对这个三十三篇的《庄子》,宋代以来的文人学者大抵以为内篇为庄子所撰,而颇有人怀疑外杂篇非庄子所作,原因是“文辞浅陋”、“虚嚣悁劣”,不像内篇那样斐然可观;近代以来随着辨伪-疑古思潮的盛行,连内篇也被认为“殆亦后学所述,未必即出于庄周之手欤?”甚而至于得出“(《庄子》)五十二篇者,盖即汉人所辑自战国至汉初之庄子一派文字之汇编。作非一手,成非一时,宜其思想庞杂,前后抵牾。”可是,就连做出这个推断的人也不能否认,“而外篇杂篇虽繁复庞杂,深浅不一,然其尤精者,如《秋水》《天下》等篇,博大精深,亦足与内篇相发明。”[34]并且所谓“庄子后学”、“庄子学派”云云,其实是莫须有的存在,查无实据,并无其人,如何能说这些莫须有的“他们”才是《庄子》的作者?今日看来,辨伪-疑古论者所言往往是模糊影响之谈,并无充分的证据。在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还是维持郭象所注之三十三篇的《庄子》为庄子所著的成说吧。我们应该看到:第一,《庄子》的内外杂篇不论多么的繁复庞杂、深浅不一,其各篇都体现出如维特根斯坦所谓“家族相似”的共同特征,而很难设想它们是出于众手。事实上,那怕是《庄子》中比较浅显的篇章,其思想之高调绝尘,后人也难以望其项背,这也就是所谓“庄子后学”查无其人的原因,即使后来好谈玄学论道的魏晋名士也只是把《庄子》当作玄谈的话头而已,并无任何超越《庄子》的思想新贡献。第二,《庄子》各篇既“家族相似”而又深浅不一,那正是因为著《庄子》者大半生围绕几个基本的思想主题“重言”不已、不断思考、反复论辩而各篇又随兴而作、续有曼衍之结果,也因此,《庄子》的思想和写作便有一个从很新锐却不很成熟的初创,到趋于成熟、畅达斯旨,直至老来颓唐、不免衰飒的过程,回头读来自然“参差不齐”了!换言之,对著《庄子》者来说,已经讨论过的问题不妨再论论,已经用过的语言话术何妨再用用,此诚所谓“已前言之而复言也”。当然,具体到《庄子》各篇,究竟孰先孰后,那还得仔细辨析,而切忌“一刀切”也。
三十年前我最初通读《庄子》,读的就是王先谦的《庄子集解》本——此书编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比较容易到手,所以购来闲时翻阅。记得读到《寓言》篇的“寓言”“卮言”之解诂,觉得都还通达,可以接受。可是王先谦对“重言”的解释,只引宣颖所谓“引重之言”,我觉得这与《寓言》篇自身的解释“所以已言也”,实在对不上号。其实《庄子》为文常说半句话,省去的就让读者去脑补,“所以已言也”的完整意思并不难补全,那就是“已言而复言之”之意,只是《寓言》篇把“复言”的意思省掉了而已。可是王先谦却把“所以已言也”解释为:“已,止也,止天下淆乱之言。”[27]这就有点刻意求深,把一个简单的词语复杂化了,所以我不大能够接受,也因此就记住了“重言”这个词语。再后来读到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和王叔岷的《庄子校诠》,也是同样的解释,仍然不能说服我。并且由于刘、王之著比较完整地引录了郭象注、成玄英疏和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由此我才发现所谓“引重之言”的解释来头甚早,王先谦、刘文典和王叔岷等大概也是遵循“疏不破注”的训诂学传统吧,所以他们只能沿着这个方向解释得越来越详密,人们也就不敢怀疑了。好在我不是专门研究古典的学者,不大迷信古训,也就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怀疑。直至读到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所附郭嵩焘的说法,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很佩服郭氏治学的实事求是。不过,郭氏毕竟是给《庄子》做注疏而非写论文,难以申论其理据,并且郭氏也与其他人一样,以“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绝句,这同样误断了句子、误解了《寓言》篇所说“耆艾”几句的意思。下面就不揣谫陋,略说个人对“重言”问题的一点意见。按说,《寓言》篇对“重言”的直接解释“所以已言也”并不难解,不就是郭嵩焘所谓“已前言之而复言也”的意思吗?可是为什么从郭象到王叔岷这些博学的古今训诂学家却要将它曲折地解为“引重耆艾之言”的意思呢?这是我多年深感纳闷的疑问。直到近年反复寻绎《寓言》篇此句的上下文,仔细比勘诸本的句读或标点,才发现历来注家都把《寓言》篇关于“重言”的几句话误断了两句——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这个古今一以贯之的句读或断句,在“所以已言也”处点断,将“是为”与“耆艾”连读,于是下面关于“耆艾”的几句话,也就成了对“重言”的正解:按照中国人的敬老传统,惟其是“耆艾”,所以“耆艾”之言也就必然被人“引重”了。这就是“引重耆艾之言”说的来历。其实,这种断句和基于这种断句的解释,乃是前人好顺着词气语调点读语句的习惯所造成的一个不易觉察的误断和一个不易发现的误解——人们顺着词气和语调读,很自然地觉得在“所以已言也”处该停顿和点断,接着把“是为”与“耆艾”一气连读,也似乎自然而理顺。可是这样断恰恰错了,而且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导致了历来对“重言”的误解。实际上,《寓言》篇本身对“寓言”和“重言”的解说,用的都是同样的句式、同样的修辞、同样的语义条理。不妨先看《寓言》篇“寓言”的解说,其辞曰:“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之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这里对“寓言”的直接解释,是很简洁的“藉外论之”,然后,庄子又用了一个比方、一段近似“寓言”的话——“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之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来间接地解释“寓言”之“藉外论之”的特点,其意诚如郭象注所说:“父之誉子,诚多不信,……辄以常嫌见疑,故借外论之。”[28]因为父子是血亲,父亲无论如何也会为儿子说好话的,所以他的好话就不大可信,可要是外人说他的儿子好,那就比较客观、比较能取信于人了。显然,父子内外关系只是打个比方来说明“寓言”之“藉外论之”之理,庄子无意、读者也不能把“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之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这几句话,当作对“寓言”意义的直接解释。比如,能从这几句话里抽象出“非父之言”或“非亲人之言”来作为“寓言”的解释吗?当然不能。庄子的这种话语套路,也同样不多不少地出现在《寓言》篇对“重言”的解说里,可是历来的句读或断句却把几句话误断成了:“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如此断句,使得同样打比方的“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几句话,变成了对“重言”的直接说明,于是年长的耆艾之言为人所重,就成了“重言”的意义之所在以至于“定义”之所是,而完全取代了或者说篡改“所以已言也”这个直接解说。弄清了致误之由,则《寓言》篇解说“重言”的几句话,就该像“寓言”那几句话一样,按照同样的话语套路和语义逻辑,把直接解释的话和间接比方的话区别开来、点断开来。下面是纠正后的新断句——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此处重新断为一句的“所以已言也是为”,是古汉语里表示强调的倒装句式,如“唯马首是瞻”之类。《庄子》里近似的话也不少,如“汤之问棘也是已”(《逍遥游》)、“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应帝王》)。然后,正如同“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之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几句是比方解说“寓言”一样,“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几句,也是对“重言”的打比方的解说:一个有阅历的人应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向后辈们言说一些生活经验与教训,且要不断言说、反复言说,成为传说和传统以传诸后世,才算没白活一世,否则再年长,也无足称道,不过是个陈死人而已——这不是翻译,只是略述大意。如此重新断句,“重言”的解释回到“所以已言也是为”,再也无须拉扯什么“借重耆艾人物以明事理之言也”来加重“重言”的份量了。顺便也纠正一下:历来对“重言”的误断所导致的另一个误解,就是把“重言”逐渐混同于“寓言”。应该说,正由于古今训诂家把“重言”误解为“借重人物(耆艾)以明事理之言”,则“重言”就必然与“藉外论之”的“寓言”相近以至相混。可有趣的是,古今训诂家对如此混同“寓言”与“重言”似乎并无什么违和感,倒是不无欣然之感。如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就引姚鼐的话发挥说:“庄生书,凡托为人言者,十有其九。就寓言中,其托为神农、黄帝、尧、舜、孔、颜之类,言足为世重者,又十有其七。”这就把“寓言”与“重言”打通了或者说“混同”了。王叔岷的《庄子校诠》也强调说:“案重言者,借重人物以明事理之言也。《淮南子•修务篇》:‘世俗之人多尊古而卑今,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所谓托古是也。”就这样,所谓“借重人物(耆艾)以明事理之言”的“重言”就与“托为神农、黄帝、尧、舜、孔、颜之类,言足为世重者”的“寓言”,达到了“十有其七”的重合度。古今训诂家可能没有想到,他们的误解所导致的这种重合,几乎取消了“寓言”与“重言”的区别,这肯定不合庄子或《庄子》之本义。说来,《寓言》篇所谓《庄子》为文好“重言”之本义“所以已言也是为”,也即郭嵩焘所解释的“已前言之而复言也”,这也并非《庄子》所独有,其他先秦诸子如《论语》、《孟子》也都不免“重言”的。这一点早就被汉学家、训诂学家发现了。早在东汉末赵岐为《孟子》作注,就发现《孟子》颇多“重言”,如《梁惠王》上篇前后两段话就是显而易见的“重言”,一是孟子对梁惠王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赵岐并准确指出:“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为齐、梁之君各其陈之,当章究义,不嫌其重也。”[29]到宋代,“重言”甚至成了儒家经典童蒙教本的一个很常见的提示标记。宋刊闽刻本何晏《论语集解》,就每于《论语》的重言处,无不夹注标出是重言。如在《学而》篇“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后,即加有“重言巧言令色鲜矣仁二,本篇《阳货》各一”[30]以提示学子。这个重言的标记,未必是何晏《论语集解》原有的,但至迟也应是南宋人翻刻《论语集解》为教本时所加。并且,这个宋刊闽刻本何晏《论语集解》于“重言”之外,还有“重意”的标注。如同样在《学而》篇“巧言令色鲜矣仁”后,又加 “重意《公冶长》‘巧言令色足恭’。”[31]甚至于这个宋刊《论语集注》书名也叫做“《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32]显然,“重意”其实也是“重言”的表现,只是不限于语言修辞层面的完全之“重复”,而扩展到思想义理层面的大意之“重复”耳。总之,这两种“重言”确为为先秦诸子所共有,而尤以《庄子》之“重言”为最甚。《庄子》的“重言”就集中表现在语言修辞和思想义理这两个层面,前者是狭义的“重言”,后者是广义的“重言”。在语言修辞层面上,《庄子》的“重言”比比皆是——诸如关于“道”或“至道”的妙论、关于“真人”“至人”“神人”的高论,关于“逍遥”与“遁隐”的美谈,反复出现在各篇中,而引用或生造的“黄帝、许由”之对话,齧缺、王倪以至于老子、孔子之事迹,这些“藉外论之”的人物、事迹、言论作为话语套术,被《庄子》各篇翻来覆去述说着、别有用心地发挥着。即如许由拒绝黄帝让天下的美谈和孔子被围陈蔡的尴尬,在《庄子》里就被拿来述说发挥了各自不下十多遍,真让人不能不佩服作《庄子》者竟能如此不厌其烦的“重言”个没完没了!如此等等的“重言”,多到数不胜数,无须举例了。再看《庄子》在思想义理层面的“重意”式“重言”,更是翻来覆去、触目皆是、不胜其重,几乎成了《庄子》思想论辩的一个鲜明特色。诸如对“道”或“自然”的本体论(存在论)之论辩,言与不言、知与不知的认识论之难题,材与不材、有用与无用的反复辨析,物之齐与不齐的价值相对论说,以及有无本末、进退得失的辩证观,……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了《庄子》反复论辩的主题,以至于《庄子》全书从逍遥自得、滔滔不绝之雄辩,直说到谨小慎微、全身避害之衰论,还是意犹未尽、喋喋不休、不肯罢休。如此这般,《庄子》全书始终围绕着几个基本的思想主题反复论辩、不断曼衍,怎能不 “重意”而且“重言”呢?正惟如此,我觉得用“反复论辩”来综括解释《庄子》“重言”之意,可能是比较恰当的。不难想象,当庄子或那个写《庄子》的人到了晚年,把历年所写各篇集中重读一遍,聪明绝顶的他自然会发现,自己的一生为文不少而喋喋不休、反复唠叨,实在重复太多了,以至于“重言”显然成了其语言修辞和思想表述之不可否认的突出特征,于是在《寓言》篇里不得不老实招认:“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这话既是坦诚的自我总结,也带有自我解释以至于自我解嘲的意味——就像一个耆艾长老必须述说自己的生活经验、方能被后辈人称道一样,自己也不得不随兴发抒、随时思考、体会自然、曼衍为文、聊以度日、所以穷年。这很让人同情。记得哲学家冯友兰曾说过,“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33]对一个能够写出《庄子》这样独特思想的哲学家来说,不断思考、反复论辩之“重言”便不得不然了。如此这般不断思考、反复论辩的“重言”进程,一方面固然由于著者始终持续思考着一些相近的思想主题,所以重复提出问题以至于重复运用此前的语言修辞如寓言典故之类,也就在所难免了,但另一方面这种持续思考与写作又不同于近人集中时间撰写所谓专著,而是随时随兴地撰写一些“卮言”性的思想随笔,所以在重复中又有所“曼衍”和发展。由此而进,对《庄子》的思想进路、文本构成以至于作者归属问题,似乎可以有一点新的理解。按,据《汉书•艺文志》,《庄子》原有五十二篇,晋郭象以为其中十九篇为后人所羼入者而汰除之,留三十三篇、编为内外杂篇并为之作注,从此流行,成为今本《庄子》之祖。对这个三十三篇的《庄子》,宋代以来的文人学者大抵以为内篇为庄子所撰,而颇有人怀疑外杂篇非庄子所作,原因是“文辞浅陋”、“虚嚣悁劣”,不像内篇那样斐然可观;近代以来随着辨伪-疑古思潮的盛行,连内篇也被认为“殆亦后学所述,未必即出于庄周之手欤?”甚而至于得出“(《庄子》)五十二篇者,盖即汉人所辑自战国至汉初之庄子一派文字之汇编。作非一手,成非一时,宜其思想庞杂,前后抵牾。”可是,就连做出这个推断的人也不能否认,“而外篇杂篇虽繁复庞杂,深浅不一,然其尤精者,如《秋水》《天下》等篇,博大精深,亦足与内篇相发明。”[34]并且所谓“庄子后学”、“庄子学派”云云,其实是莫须有的存在,查无实据,并无其人,如何能说这些莫须有的“他们”才是《庄子》的作者?今日看来,辨伪-疑古论者所言往往是模糊影响之谈,并无充分的证据。在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还是维持郭象所注之三十三篇的《庄子》为庄子所著的成说吧。我们应该看到:第一,《庄子》的内外杂篇不论多么的繁复庞杂、深浅不一,其各篇都体现出如维特根斯坦所谓“家族相似”的共同特征,而很难设想它们是出于众手。事实上,那怕是《庄子》中比较浅显的篇章,其思想之高调绝尘,后人也难以望其项背,这也就是所谓“庄子后学”查无其人的原因,即使后来好谈玄学论道的魏晋名士也只是把《庄子》当作玄谈的话头而已,并无任何超越《庄子》的思想新贡献。第二,《庄子》各篇既“家族相似”而又深浅不一,那正是因为著《庄子》者大半生围绕几个基本的思想主题“重言”不已、不断思考、反复论辩而各篇又随兴而作、续有曼衍之结果,也因此,《庄子》的思想和写作便有一个从很新锐却不很成熟的初创,到趋于成熟、畅达斯旨,直至老来颓唐、不免衰飒的过程,回头读来自然“参差不齐”了!换言之,对著《庄子》者来说,已经讨论过的问题不妨再论论,已经用过的语言话术何妨再用用,此诚所谓“已前言之而复言也”。当然,具体到《庄子》各篇,究竟孰先孰后,那还得仔细辨析,而切忌“一刀切”也。
2021年10月15日—11月6日草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注释
[1]郭庆藩:《庄子集释》第749-750页,中华书局,2004年。
[2]郭庆藩:《庄子集释》第751页。
[3]郭庆藩:《庄子集释》第750页。
[4]郭庆藩:《庄子集释》第751页。
[5]郭庆藩:《庄子集释》第752页
[6]王先谦:《庄子集解》第190页,中华书局,1987年。
[7]王叔岷:《庄子校诠》第828页,中华书局,2007年。
[8]程树德《论语集释》就于“无莫也”句后引陆德明《经典释文》云:“莫,郑(郑玄)音慕”,并申言:“郑读莫为慕者,慕从心,莫声。古本省作‘莫’耳”。——见《论语集释》第320页,中华书局,2017年。
[9]朱熹:《四书集注》第109页,中华书局,1983年。
[10]普济:《五灯会元》第67页,中华书局,1984年。
[11]普济:《五灯会元》第559页。
[12]释静、释筠:《祖堂集》第789页,中华书局,2008年。
[13]释开著、魏道儒释译:《禅宗无门关》第101页,东方出版社,2017年。
[14]司马迁:《史记》第2139页,中华书局,1982年。
[15]郭庆藩:《庄子集释》第711页。
[16]彭铎:《文言文校读》第12、13、9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
[17]彭铎:《文言文校读》第96页。
[18]郭庆藩:《庄子集释》第947。
[19]宣颖:《南华经解》第18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20]郭庆藩:《庄子集释》第947、949页。
[21]宣颖:《南华经解》第189页。
[22]王先谦:《庄子集解》第245页。
[23]王叔岷:《庄子校诠》第1088页。
[24]郭庆藩:《庄子集释》第947页。
[25]郭庆藩:《庄子集释》第949页。
[26]郭庆藩:《庄子集释》第947-948页。
[27]王先谦:《庄子集解》第245页。
[28]郭庆藩:《庄子集释》第948页。
[29]赵岐:《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本第2671页,中华书局,1980年。
[30]何晏集解:《宋刊论语》第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影印,2008年。
[31]何晏集解:《宋刊论语》第8页。
[32]何晏集解:《宋刊论语》第7页。
[3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见《三松堂全集》第6卷第30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34]齐思和:《<庄子引得>序》,见《庄子引得》第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解志熙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清华文学研究”栏目旨在推介清华学人在文学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促进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