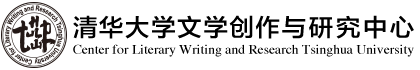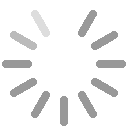青年作家创作谈 | 董夏青青: 收拾精神,自做主宰
2022.04.28
在4月16日晚举办的“清华大学朱自清文学奖(2021)颁奖典礼”上,青年作家董夏青青作为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办的“清华大学青年作家工作坊”首期成员,受邀参加活动,并与现场师生分享创作经验,以下为发言实录。

很荣幸能受邀参加这一届的“清华大学朱自清文学奖”颁奖典礼,并作为嘉宾发言。首先,向各位获奖的同学表示最真诚的祝贺!
本科时,我在中关村南大街上的原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夏天,会跑来清华大学看荷花,羡慕走在校园里的每一位清华学子。直到2018年7月,我有幸参加了由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和《收获》杂志社共同主办的“2018清华大学作家工作坊”,才体验到在清华校园里听文学课以及谈论文学,是一件多么振奋和幸福的事。
现在回想,2018年的那个夏天太珍贵了。没有疫情,也没有世界性的紧张感。我在课堂上听格非老师讲康拉德时谈到地球无限性的消失,说作为一个文学性象征,大海已经不再代表无限,而与精确的地缘政治相关联,人们正面临着海洋秩序、数码秩序以及生命秩序的争夺,但当时的我还未把格非老师谈到的这些,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挂上钩;那时,西渡老师在课上说,每每听到同学离世的消息,就觉得自己跟世界的关系正在某一刻变得疏离。而当时的我也不会想到,仅在两年后,我就要写下一篇关于牺牲和理解牺牲的小说。非常具体地体会到格非老师在课上说的那句话:“必须有一个沉念在心中,否则都是游词。”
前年,我在前线采访时认识的战士当中,有一名老家甘肃的士官,为了给自小体弱多病的妹妹治病,供妹妹读研究生,而自己中断了本科学业,参军入伍;有一名特战旅班长,用湖南的家乡话告诉我,他父亲曾经外出务工,受工伤后回家一直卧床养病,家里越来越穷,被同村的人看不起。父亲曾对他说,自己已是半截入土的人了,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儿子在部队干出个人样来,让家里人能在村子里抬起头来。为了给父亲和家庭争得荣誉,这名班长凡事冲在最前,他说因为自己岁数大,已经错过了考学提干,为此,他珍惜每一次冲锋的机会……
我还认识了一名排长。在一次事后登上新闻的对峙冲突中,这名排长的一条胳膊和一条腿被打断了,头破了一直流血,徘徊在失去意识的边缘。后来援兵到了,清理战场时,这名排长被人绑在两个拼起来的盾牌上,抬进了医疗帐篷,之后又由直升机运送下山。执行任务时山里没信号,他的手机也在行动那天被摔碎了。但联系不上孩子,排长的父母焦急无比,他母亲急得通晚失眠,然后邻居就给他们家介绍一位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说,您儿子在西北方向,受了皮肉之苦但还在喘气。这句话,让他母亲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去年年初,一直躲着不和父母打视频电话的排长终于回家休假,在机场,母亲一看见他走过来就蹲下大哭。排长说,可能我和战友们朝夕相对,也不觉得自己晒得多黑、身上的伤疤吓人,可是一回到家照镜子,就被镜子里的自己吓了一跳。但经历的种种,除了战友,他们对身边亲人一个字也不能提及。他说在家的某一天,当他蹲在步行街的麦当劳门前吃冰淇凌,看着行人来来往往时忽然觉得,这一年里,他们所经历的种种是否被人知晓、理解和尊重,并不值得计较,重要的只是去做、去行动以及去记住已经离开的人,并坚定地保护这些记忆留下的情感,保存应当由我们负起责任来保存的记忆。如此一来,就像西塞罗所说的,“虽不见友,而其音容如在眼前,虽有需求却不感缺乏,虽应虚弱却依然强健,更难言诠的是,虽死犹生。”
写作这篇小说期间,我翻看了18年7月17号,杨立华老师给我们讲课的笔记。杨老师说,只要你是作为人的存在就一定具有主动性,人的主动性就是超越和改变,而把生死看作分内事和等闲事。
在2018年后至今的这段时间,我总会问自己,文学最大的功用是什么?我想,在面对接踵而至的种种对于人的考验,写作首先就是沟通和理解。一方面是我们选择了写作这种生活,另一方面写作也引导、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写作让人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让我们得以接近平时接触不到的人和事,唤起共情与共识。疫情期间,写作和阅读甚至成为我们与世界往来最直接的方式,我们正是通过写作和阅读走向开阔之地。当资本、科技、疫情“让人与人之间链接的可能性越来越聚焦在空间、资源的竞争与倾轧上”,一个人对另一个具体的个人越来越没耐心,有时候甚至一个家庭内部也是如此时,文学抚慰人心的功能也更为凸显,有时几本好书、一封书信,即是最切实的安抚和慰藉。钱穆先生说,“心走向神,走向物,总感得是羁旅他乡。心走向心,才始感到是它自己的同类,是它自己的相知,因此是它自己的乐土。”而“心走向心”这一看似简单的壮举,很多时候都是依靠文学来实现的。
我曾在北疆伊犁见过哈萨克族的驯鹰人,在哈克萨族老乡们看来,只要鹰还在空中飞翔,他们的勇气和力量就不会枯竭。而对于人类而言,只要故事和讲述故事的决心还在,精神与文明的血脉就在,于困境中“收拾精神,自做主宰”的那份魄力就永远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