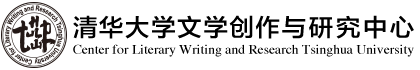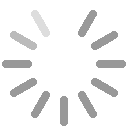未尽的生活——在美国疫中的笔记(2020文学奖一等奖)
2021.06.02
作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何青翰 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本人。
上帝为每个灵魂提供了选择机会:或是拥有真理,或是得到安宁。你可以任选其一,但不能兼而有之。
——Ralph Waldo Emerson
九月中旬,在烈日熏烤的森林腹地,我沿着杜克大学周边石砌的矮墙慢步前行。每隔半分钟,我会确认一次谷歌地图给我的指示方位。不久,我发现了目的地:在树荫浸透的校园建筑里,有一座朴素的小楼,周围花丛稀疏,它就那样平静地闲卧在草坡上。在此之前,我并没有见过David Wong老师。我们曾经隔着大洋通话,他费力地辨析我拙劣的英文发音,并且询问了我对于先秦时代诸子所论“道德动机(moral motivation)”的理解。其后我一心忙于暑期实践以及处理出国手续,奔波往来,再没有诚心诚意和他讨教过问题。David Wong老师在1977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其后辗转任教,2000年之后,他获聘于杜克大学哲学系,从此留在了杜克。他自青年时代起即努力地对先秦哲学充满兴趣,尤其是荀子与庄子。
于是我就这样走到了Wong老师的办公室门前,整整衬衣,敲门,没有答应。再敲门,还是没反应。我心想是不是自己看错了时间,助理忙过来说:老头不在。过了半个小时,Wong老师来了,天气太热,他一进办公室就脱下了外套。他面色谦和,清瘦而高大,两鬓雪白,眼神极为深邃,笑起来温厚而收敛。我颇为激动,讲了很多感谢的话,然后告诉他,我正在阅读Natural Moralities和Moral Relativity,这是他的两部代表作,可惜至今没有汉译本。其中论述的“道德”与“普遍性”的关系,以及世俗生活的价值取向,贯穿了他大半生的思考。他很高兴,让我加入他的讨论课,再拓展一下目前的想法。他也很好奇,彼岸的“儒者”正在做些什么。
从那以后,我会不定期地去办公室见他并请教相关的问题。我很喜欢坐校车从杜克大学的西区到东区,沿途公路起伏,两侧巨木参天,阳光透过幕布般的枝叶,在拥挤着学生的车厢里扫过,幽明一瞬,像是时间的颜色。这样的交流持续了很久,直到疫情大规模爆发,全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谁也没有想到,那些原本局限于课堂讨论的抽象“概念”,诸如自由、生命、美德,会像陨石暴雨一般坠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摇撼着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一,人权,过时的议论?
一九年的秋季,Wong老师开设的课程名为VALUE ACROSS CULTURE,讨论主题介于政治文化与伦理生活之间。讨论的地点就在哲学系的三楼,教室没有窗户,四壁挂着写满了各种符号的黑板。青年时代的Wong老师亲历学界前辈对“规范”伦理学的纠正,受其影响,他关切重心既不是抽象概念的形式化推论,也不是单纯的语言分析。为了规避伦理学的“无意义”,他引入了大量关于美国本土的宗教、教育、舆论、选举制度的讨论文本,并且始终将儒家思想作为一个主要的对话者。就像Wong老师所说的,启蒙思想家试图以理性为世俗立法,其结果却是将“伦理学”变成了切除人类本有道德常识的手术刀。这个比喻让我想起了《飞跃疯人院》的结尾剧情,被摘除脑叶男主最终驯化于疯人院的规章制度,这意味着他不再犯错,也就不再是一个“人”。以抽象的人类理性代替鲜活的历史存在,继而发明一整套冰冷的道德“律法”,现代伦理学正在变为一位消灭异己的“暴君”。因而,在Wong老师的精神世界里,与孔子、老庄所进行的交流,正是返回日常生活的最好办法。
在Wong老师开列的书目中,Joseph Chan(陈祖为)在前些年出版的Confucian Perfectionism: A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Modern Times是第一本书 ,国内将其译为“儒家致善主义”。Chan的写作背景是后殖民时代的香港,他声称自己必须在儒家思想的范畴内有效回应现代政治的根本法则。Wong老师告诉我们,他倒不觉得Chan的调和工作有过多高明之处,但他欣赏Chan能够直面“民权”抑或“人权”对于传统儒家思想的根本挑战。在援引康德哲学的前提下,Chan宣称儒家伦理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道德自主观,这种自主(autonomous)孕育着独立人格,与自由意志等价。这未免强词夺理了,现代自由所强调的乃是“消极自由”,这也就意味着价值的成分取决于个人的选择。换言之,仁义礼智的道德价值对于儒家而言是永恒而确定的,如荀子所说“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所谓儒家式的自主乃是相同目的地所提供的不同路径,而现代自由则是一切开放,你既可以四面出击,也可以毫无目的地原地滞留。连Chan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我将他对儒家伦理的看法朴素地归纳为:太多义务,太少权利;太多秩序,太少自由。与此呼应,Wong老师认为,在传统儒家的道义系统中,几乎所有与现代生活相冲突的内容,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归纳为儒学与“人权”(human right)的冲突。狄百瑞、安靖如等汉学家,无不以处理人权与儒学的冲突为头等大事。
我接触的美国同学不算少,对中国保持严苛态度的人实在不多。他们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并没有太多兴趣,比之于中国学生对美国历史文化的理解程度,美国学生的中国知识往往是相当匮乏的。毕竟,他们觉得自己身处的国家才是“中央之国”(the center of the world)。来自韩国的Mr Kang经常安慰我,因为不止一位美国同学在闲聊时自信满满地告诉他:韩国的总统的名字叫做“金正恩”。
在我的印象里,David老师在课堂上从不评论当下中国,也没有刻意赞美“人权”。他引用孟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以反对毫无节制地将“人权”与“人性”等同。他提醒同学们,“人权”似乎更像是一个现代人与古代生活对峙的阵地,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教条或定论。话虽这样说,但“人权”毕竟也是流血换来的。在美国的文化语境中,“人权”已经凝结为一尊无法撼动的政治神祗。
我对此极感不适。在课间,我尝试单独询问 David老师:“您是否知道‘人权’这个概念在许多地方早已声名狼藉?”David老师再一次显示了宽厚的笑容,他说:“There are objective constrains on moralities as human inventions in a way analogous to there being objective constraints on bridges.”(作为人类发明,道德有其客观约束,亦如桥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不主动引导课堂的讨论偏向于一个答案,看着年轻人之间的奋力争辩,他欣然而沉稳。David老师的青年时代,恰逢美国民权运动如风起云涌。他缄默无言的时候,我总是会在他的旁观里,看到对学生的某种期待。
根据他的观点,“人权”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理应作为备用的守护手段,而非一种能够随时在场的必要的美德(virtue)。他举例说,在家庭中,成员的行为通常是出于“爱”或对其角色责任的承诺,如母亲、祖父、女儿或兄弟,而不是出于对其他成员行使权利以及如何维权的担忧;我们应该考虑合作,而不是对抗。这就像是课程讨论的Justin Tiwald的Confucianism and Human rights,这篇文章的核心在于其开篇第一句话:
One of the most accessible ways to wrap one’s mind around the controversy over Confucianism and human rights is to consider what would happen to a well-functioning family if it instituted many of the same practices as rights-protecting societies. (要理解儒家思想和人权之间的争论,最容易的方法之一就是思考,如果一个正常运转的家庭采取了许多与维权社会相同的做法,那么这个家庭将会发生什么)。
奠基于抽象的个体理性的“人权”观念,无论在常识上,还是在学理上,都无法顺畅地运用于正常人的家庭生活,过度的权利意识反而会加剧现代家庭的内部分裂,推而广之,其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内战,演变为不流血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Wong老师对此大为推崇。我很兴奋,于是问他,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传统人伦的基础上重建现代生活的价值意义。Wong老师在听懂了我的话之后,回答很明确:不行。我为此懊恼了好几天。由此可见,在他的眼中,面对“人权”观念的取舍之间,真正的敌人是一种外在而强迫的道德垄断。反过来说,如果这个垄断者是儒家礼教,他也不会认同:既然赶走一位“暴君”,就不要再迎来另一位“暴君”。
二,儒、道互补的多元主义
Wong老师的比喻让我想起了查尔斯·泰勒的一个论断:如果要说有什么是现代人再也无法接受的古代事物,那就是君权神授。现代革命在精神上斩断了君主的头颅,而激进的思想家则宣称“上帝已死”,也就等于否认了客观而外在的道德权威,将人生意义的选择权交给了每一个人。在敞开的历史机运面前,伦理学的专家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清醒地认识到伦理学抑或哲学本身的限度,帮助人们通过“审慎思考”而决定自身伦理生活的计划。因而,Wong老师对于现代“人权”与古代“人伦”,均未视为神圣而永恒的法典,而是在伦理生活的范畴下,“权利”与“义务”的不同侧重。因此,当我向他提出中国大陆有些学者倡议恢复儒家式的家庭伦理及其社会权力,以父子关系为中心,重塑长幼之间的等差之爱,他当然不会认同。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假如所有的选择在价值意义上都是平等的,那么唯一可以确定的价值也就只剩下“自由”。选择什么并不重要,人生本来就没有神圣的目的,“选择”才是关键。这种不可让渡的自由,根源于欧洲文明对宗教战争的深刻反省,以追求真理之名而清除异端的行为造成了无数的悲剧。假如“人权”是钞票上的许多“零”,包括生命、财产等等,那么“自由”才是赋予其价值的“一”。宏观上看,这当然是一种可贵的进步。但这种“进步”所包裹的负面效应也很明显,伦理生活的“自由”会逐渐掏空伦理生活的内在意义。最终,只剩下“形式”。
“自由”比生命更重要吗?如果确实更重要,那么是何种“自由”?不久之后,出题者来了。只不过,这次的“讨论课”的地点并不是这间没有窗户的教室,而是全世界。
事实上,此后纽约以及加州陷入新冠病毒的大爆发,州政府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仍旧是要求本州人民尽量居家隔离,停止工作以及集会。这个并不过分的防疫措施立刻遭到了大批美国本土人士的反对。为什么呢?病毒虽然恐怖,但生死考验毕竟还没有出现在眼前,而居家隔离,失去行动自主,那就是赤裸裸地剥夺选择的“自由”,从而毁灭了美国精神的根源。作为一个深受实用主义熏染的中国人,我自谓生平第一次真正见到如此“勇敢”的国民,颇感瞠目结舌。
那么Wong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在Wong老师的著作中,尤其是Natural Moralities,反复探讨了一个伦理学的基本困难:道德价值及其原则究竟是普遍的、一元的,还是独特的、多元的?在Wong老师以前,这个困难已经消耗了无数的心智与真诚。在1980年代,他曾经坚持讨论“相对主义”(relativity)之于道德生活的意义,毫不意外,他受到过来自学界的诸多诘难。坚持“相对主义”无疑需要承付巨大的压力,因为这意味着人们会愤怒地指责你试图为那些落后、愚昧的地方陋俗进行辩护。依据相对主义的推论,倘若那些身处于非洲、太平洋等蛮荒之地的居民仍在坚持“吃人”的习俗,抑或19世纪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我们亦不能横加干涉。因此,相对主义意味着:我们从来无法获得绝对的、单一的道德律法,也不存在永恒的道德价值。有鉴于此,Wong老师在Moral Relativity一书中为论证一种健康的“相对主义”所付出的努力,自然有他的独到之处。
首先,他认为任何一种道德体系都不应该垄断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有权利根据具体的生活经验来选择自己的价值方向。人类历史已经多次所谓的“绝对真理”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单一、独断的道德权威最后往往沦为窒碍人类的枷锁。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主义的功能就是促进道德生活的开放状态,允许伦理规范不断进行自身调整、优化。其次,他认为我们应该在身份平等的前提下,重塑一个新的富于实践性的道德观念:它既不依赖于武断的、先验的真理观,也不依赖于个人欲望。也就是说,道德信仰应该是文化的历史发明,文化传统将填充由道德原则所构建的生活空间。原因很简单,原子化的、只讲权利的个人,没有可能构成“生活”。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理解“相对主义”的同时,提倡价值的多元主义(pluralism)。“多元主义”观念对于Wong老师的整体研究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变。由此,他从八十年代的Moral Relativity(《道德相对主义》)的思路转向“多元主义”的视角。
这种视角其实很好理解。简而言之,人类文明发端于不同的社群文化与自然环境,道德、伦理的价值与原则往往是不可公度的,甚至是互相冲突的。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善恶对立来解释这种冲突;也不能用进化论的线性视角来判断孰优孰劣。任何适当的道德体系都必须包括调和道德分歧的态度与办法。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怀抱积极心态参与社群建设。换言之,我们要承认人类实现自身价值的不同形式,既然大家同处于一个共同文明体或共同社会的框架下,就应该通过不断的对话与思辨,达成开放性的道德共识,拓宽我们面向有意义的生活的道路。这个方案,既避免了思想专制,又克制了价值虚无,看起来两全其美。但是,如果“文化传统”的理念无法以社群的形式落实下来,如果多元价值演变为个人的自说自话,那么这个诉诸于“对话”的思路就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毫无实践能力。正是在这个关节,儒家与庄子在Wong的伦理学研究中变得举足轻重。
在我看来,他从先秦哲学中提炼出“教化”(cultivation)的概念,以此进一步阐释“自然的道路”(naturalistic way),与民主社会的平等、自由,合在一起,拼凑出一个和谐的道德图景。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类生活或许根植于某种天赋,但在外界影响下,相同的情感与理性却不一定会促成美德。因而,尽管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他们更需要美德的教育与思考的训练,才能辨析生活,实现有价值的选择。故而《礼记》中说:“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人格的自觉只不过是生活意义的起点,儒家的教化传统所蕴含的“修身”以仁、礼为本,推己及人,反对以私废公。《论语》的开篇第一个字就是”学“,而《荀子》的开篇即为《劝学》。这些品质,与宗教式的顿悟、启示,有着很大的差异,理应在民主时代的开放社会中理应产生更多效用。毫无疑问,孔子在Wong老师的心里虽然不是掌握宇宙真理的救世主,但至少也是伟大的圣贤。针对儒家“教化”中过强的礼教成分,Wong老师除了以特殊“文化传统”的定义予以肯定,则援引道家思想加以平衡。于是庄子就在这里出场了。
我想他是真正地极爱着庄子,当他谈到动情之处,眼神里的向往与钦慕,甚至超过了论及孔子的情形。他赞美庄子以体会宇宙天地的超逸精神观察人间的政治,无论是《逍遥游》抑或《齐物论》,都超越了“生存”意义,并消除了那些腐蚀礼乐文化的权力之毒。“道”即宇宙秩序与人类心灵的源泉。在庄子的眼中,万物各有所归,不同道德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如何面对自然之“道”的完整与丰富,或取于彼,或舍于此。人与鸟兽草木皆为自然的一个部分,唯有“自然”收束时间,为多元的事物提供活动的意义。Wong老师写道:We are compelled to recognize that others embody real values just as ours do. In this strain of argument I am highlighting, then, Zhuangzi’s appreciation for diversity is a moral stance at the same time that it constitutes a distancing from one’s own original moral commitments.(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他人也如我们一样体现着真正的价值。因此,在我所强调的这一论点中,庄子对多样性的欣赏是一种道德立场,同时它保持了与个人原初道德承诺的距离。)庄子寄予我们的并不是取消“道德”的自我放逐,而是在选择道德信仰的同时,从他人的眼睛里,看到更多的美好,寻找更寥廓的世界。我想这种以他人视角出发的心灵体验是必要的。即便我们个人以道德或者说美德去顺应“自然”的内在精神,亦不能彻底理解那些无法为科学所控制的幽暗力量——譬如一种无迹可寻的病毒——更何况全部的“自然”。
三,世间哪得双全法
三月刚过去了两周,我来到图书馆门口。在门环边,我看到了一张并不起眼的布告:由于新冠病毒的扩散,杜克大学所在的北卡罗来纳州宣布全州封闭公共场所,建议居民实行居家自我隔离。大家给Wong老师去信,他回信让同学们安居在家,保持邮件往来即可。于是,朋友们消失了,无论是访学、留学的国内学生,还是哲学系的美国同学,甚至连小区的物业经理,那个喜欢饶舌的老叔,都不见了。渐渐的,杜克校园里的花开了,河流映照着春天的蔚蓝色,松鼠飞奔在空旷无人的草地上。但这个时候居然又下了一场春雪。夜里,雪花纷纷扬扬,敲打车窗。次日清晨,素洁的雪层与青翠的灌木相互映衬,沿着林中路疾驰过去,满目银白。不久,日光倾泻而下,把屋顶上、树干上的白雪渐渐消融。与此同时,病毒正在悄无声息地侵蚀着无数的生命,老人、少年,市议员、穆斯林、工人、文学家。
回想新年之初,国内的情况愈演愈烈,坏消息纸片一样飘洋过海。在杜克上学的朋友们一起在春节聚餐,暂离隔岸烽火,茶酒一碗一碗地斟满,思绪浓稠,怎么也冲不淡。打开手机,朋友圈充斥着情绪亢奋的檄文和悼文,无法预见乐观的前景。政治学系的朋友给我发来一篇无法打开链接的文章:《论贤能政治的破产》。但我仍保持着冷静,这倒不是因为我看起来暂时置身事外,而是因为我对中国的基层治理能力稍有体会。我告诉我周围的美国同学,一旦中国大陆动员起来,事情或许很快就会发生剧变。果不其然,当疫情转入下半场的时候,随着中国大陆的疫情得到纾解,欧美成为了主角。而这一次,我们没有看到雷厉风行的交通封锁以及全线开动的医疗物资生产。除了照例进行的政治评论,美国一切如故,平静得令人忐忑不安。
还在秋季讨论课刚刚结束的时候,我带着Wong老师的著作去找他。我表示自己在阅读他的文章时,真切地感受到他对于传统儒学与庄子在理智上的热爱,由是之故,我再一次向他请教关于重新理解儒家人伦的问题。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传统东亚文化圈内,人伦关系是宇宙秩序的人间代表。现代革命虽然结束了君主制,带给了我们普遍的身份平等,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日常生活的伦理趣味,我们失去了“家”。也许我们可以在继承革命遗产的基础上,尝试恢复儒家人伦的内涵,以“敬爱”、“孝悌”调和过于僵化与刚性的公民定义,减缓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张力。
Wong老师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发言,然后平静地说:“你说的很感人。我先不讨论基督教社会与儒家社会的差异性,我记得我在Natural Moralities里讨论过舜的故事,你当然比我更熟悉。舜是国王,为了挽救杀人的父亲,放弃了王位,带着父亲逃到了海边。你怎么看待舜违背司法正义而选择维护孝道的行为?”我的确熟悉这个颇多争议的圣王事迹,却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我只是说古代中国的圣王往往要经受许多考验。Wong老师也没有追问,他只是告诉我他的答案:在他看来,在舜的故事中,孝道与正义的矛盾并不是让我们偏向于孝道抑或正义,而是启示我们,人类生活在一个有着道德分歧的张力的现实世界中,舜的伟大在于,他依据道德的自由做出了自己的决定。说这话时,走廊的窗户透进来一束亮光,Wong老师神色温雅,略带悲悯,宛如庄子。
我并不认为Wong老师完全理解了“窃负而逃”在儒教经典中的意义,也不能确定他触及了我的核心问题。但我大概明白了他为什么既要寻求道德共识,又从未试图将寻求道德共识的希望寄托于复兴某种形态的道德传统。多元主义之所以成为他坚决捍卫的精神堡垒,虽不乏学理的依据,但归根溯源,仍然与他脚下的这片土地息息相关。一百年前,当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意图在精神上完成“弑父”的时刻,彼岸的美国,正旁观着即将堕入血泊的欧洲;1917年,马克斯·韦伯发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反省了近两个世纪的启蒙理想,希望以此激发知识分子承担悲剧宿命的勇气。此后几十年间,美国以极其博大的疆土接纳了来自欧洲各地的思想流亡者,在这些日后形成美国学术研究高度的“遗民”眼中,即便美国缺少优雅的古典学根基,更没有精致可观的文明遗迹,但她毕竟没有滋生法西斯主义那样的人间恶魔,在这里生活着的除了冷血的资本家,更多只是托马斯·杰弗逊笔下那些作为清教徒后代的淳朴的“乡民”。因此,即使“自由”这个词汇早已为庸俗的利己主义者扭曲、污凃、滥用,“自由”的生活却仍然值得人民守护。而今,新冠病毒对这种生活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以及超过了曾经的纳粹德国。纳粹德国的暴力是有形的,而扩散的病毒是看不见的。
自四月至五月,失控的局势再也无法被掩饰了。在美国全境,新冠病毒确诊感染人数逐日暴增,各个州先后陷入史无前例的公共恐慌。由于医疗物质短缺与各州之间匮乏有效的合作,政府根本无法遏制疫情,整个美国社会宛如脱缰野马般冲向不可预知的灾难。不久之前,我和朋友们拼命搜集口罩寄回国内;现在,国内的家人和同学觉得我身陷于一个朝不保夕的毒区。纽约医院的惨状吓坏了所有人,能够囤积的物品都遭到了抢购。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内部还在争论戴口罩是否涉嫌妨害个人自由。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过神来。
春节前我曾与朋友们南下千里,途径奥兰多,参观了美国航天发射基地。NASA保存了阿波罗11号的火箭发射架,它仍旧屹立在原址,宛如钢铁铸造的丰碑。回顾这个当代“神话”,冷战的权谋都已经尽付尘土,在宇宙面前,人类选择记住的是自己孩童般的勇气。而今,那个当年完成登月、民气高昂的美国到哪里去了?这个号称在政治上最为完善的民主国家,正眼睁睁地看着疫情扩散而推诿责任。即便坐拥有最先进的医学科技,各州仍然会出现严重的医护短缺。就在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以“What is a society that has no value other than survival?”的发问对政府颁布的居家隔离表示反对的同时,德国韩裔学者韩炳哲提出,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防疫成功,与儒家文化的根基有着直接关系。他说,东亚国家的文化条件利于专制的,人们比欧洲人更顺从、服从,也更信任国家。最重要的是,亚洲人从不忌讳使用无孔不入的科技监控来对抗病毒。除此之外,也有人认为,儒家社会把“家”看做生活的核心,所以他们更能够长久地“居家”。这样看来,病毒的狡猾之处,就在于它能够通过寄生的方式将”人民“变为”人民的敌人”,这就把人类与病毒的较量,异化为了自由与权力的博弈。
四,美好生活与人民
依照Wong老师对儒家美德理解,我想他绝不愿意将儒家社会特征单纯地等同于韩炳哲所说的专制与服从,这恰恰是与他所坚持多元主义相违背的。韩炳哲的描述,实际上更类似于先秦的法家思想。但他也承认美国民主政治的严重败坏。在去年的课程中,他在汗牛充栋的美国民主批判中挑选了Jason Brennan所著Against Democracy(《反民主》)作为讨论文本。Jason Brennan认为民主制度底下的“人民”(we the people)只存在三种人:第一,追求世俗快乐,无心公共事务的“哈比人”;第二把政治作为娱乐赛事,天性狂热,且自己个人意识形态的好恶作为政治活动唯一标准的“政治流氓”;第三,极少数的客观、理性,关心公共事务,富有知识且善于倾听与沟通的“瓦肯人”。”“哈比人”和“瓦肯人”的借代来自《星际迷航》这样的美国流行文化中电影形象。
在许多民主设计师的眼中,以选举制、代议制为核心的民主生活所预设的基本受众其实只能是作为社会精英的“瓦肯人”,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充斥公共生活的人,大部分都是冷漠麻木的“哈比人”以及狂热偏激的“政治流氓”。投机的政客正在利用这种麻木与激情,假公济私,将民主生活带入堕落的深渊。Wong老师并不反对用这个分类来应对美国民主政治生态,其实略懂古典政治思想的人都看得出来,这个略带嘲讽的比喻实际上来自柏拉图《理想国》将城邦政治的灵魂划分为“欲望”、“激情”、“理性”。自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几近破产之后,反思美国民主政治的著作层出不穷,Jason Brennan的写作卑之无甚高论,只不过他将矛头直指被视为民主核心的选举制度,胆敢倡议缩减选举人资格,重塑精英政治。而戳中Wong老师神经的正是这一点:Brennan指出,只有当人民具备充足的政治信息以及社会知识,才能辨析何为政治价值,并通过慎重的投票加以实现。在现实中,绝大多数的人民都有着严重的知识贫血,任凭情绪与偏见主导行为,以无知之人决定政治的方向,乃是一种真正的不正义。
我们将Brennan的这段分析转化为伦理学语言,就能发现这也正是是Wong老师对于消极的道德相对主义的诊断。如前所述,泛滥的价值平等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价值的取消,美德将为欲望所代替,造成民主社会的整体性败坏,从而连带着将“多元主义”在内的一切自由精神的品质卷入垃圾堆;而知识分子则将被隔离在社会真相之外,被权力和资本豢养成空洞符号的生产机器。在疫情越发严重之后,这些忧虑在他给我的复信中常常溢于笔端,他写道:
“The reason why the choice seems to be economic livelihood versus lives of the most vulnerable is that here in the U.S. we make most people struggle to earn a living even though we have enormous resources and wealth here. ”(之所以选择经济生计而不是最弱势群体的生活,是因为在美国,尽管我们拥有丰厚的资源和财富,但我们让大多数人难以谋生。)It is because people are so vulnerable here that there is so much pressure to resume the economy and the “normal” way it exploits people and leaves them to care for themselves.(正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太脆弱了,才有那么大的压力要求恢复经济,以便他们得到“正常”的方式的剥削从而养活自己。)
我原以为民生问题并不能真正引起Wong老师的情绪波动,毕竟那些衣食住行的困扰与学院的学人相隔甚远。但我错了。他对于劳动人民有着真挚的同情,绝不带表演性质与救世主心态的那种同情。他深知美国社会那层耀眼的光环之下根深蒂固的资本压迫,与瘟疫相比,普遍的失业也许将造成更严重的绝望。看到美国的政客们把这场危机当作另一个让人们彼此对立的战场,他深感难过。这里的困难已经超出了伦理学的讨论范畴,在排山倒海般涌来的瘟疫面前,作为概念的“善”与“恶”、“一元”与“多元”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五月底,明尼苏达州的黑人弗洛伊德遭到警察虐杀,示威游行席卷全美,各持己见的人民互相攻击,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自南北战争以来,这样的剧情持续了近一百五十年,此后仍旧会一轮接着一轮的上演。
可想而知,这就是亲历过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Wong老师为什么会一边服膺庄子,一边真诚而迫切地关心儒家的“教化”,申述人性的复杂。失去美德教育的民主生活将泯灭知识的尊严,纵容无德的领导者,威胁那些累积了数百年的公序良俗,从而破坏民主政治的自我更新能力。重视“教化”的内容包含两点,首先,将人性作为生活秩序的起点而非结果,顺应人性中的善良与理性,抑制人性中的自私与暴虐;其次,拓展教育的公平性,有教无类,使每一个人参与政治生活的人具备充足的知识与美德。只有恢复人民的美德,民主生活才能真正处理危机,民胞物与,选贤任能,为缓慢的进步提供基础的条件。
这个诉求击中了现代民主政治的要害,它的理据来源于儒家传统,但不限于儒家传统。只不过从前需要是“教化”君主,现在所要做的是“教化”人民。由于对人群集聚的限制,七月的独立日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市区燃放焰火,周边的住户自发引燃了许多汽油桶,转瞬即逝的火苗与混乱的车流打碎了时空的宁静。层云和硝烟散去之后,月光朗照。我想到了许多往事,在历史的长河里,个体的悲欢何其短促,我们为遥远的不知名的人付出廉价的同情,却往往对生活内在的平庸毫无措意。在这个问题上,我特别能够感受到Wong老师的勇气。这种勇气不同于追求纯粹知识的执着,而在于他灵魂深处对“生活”的承担而非厌离。惟其如此,即便他所捍卫的价值属于现代人,但他似乎彰显了儒家士大夫的精神气质,以一种低调而曲折的方式。
我将这个想法通过邮件告诉他,他拒绝了我的比附。我已经习惯了他的谦逊,但我追问道:这是为什么?他说,他不知道应该由谁来执掌这“教化”的权力,就如他不知道这场瘟疫会给我们留下什么。他期待着这场可怕的危机将促使大家为广大民众、而不仅仅是特权精英采取一种更好、更安全的生活方式,但他并不乐观。当然,如果“人民”是历史的归宿,他更不认为美国民主的命运就是民主的命运。在深夜里,看到他的这封复信,我心里忽然感到了一种释然:在我心里,总是执念于一个大写的“一”,而在他心里,一个普通的美国的知识分子的心里,总是记挂着一个大写的“多”。于是我打开了冰箱里仅存的啤酒,以慰良夜。此时,美国的新冠病毒确诊人数已经超过百万。我心知肚明,在我回国之前,恐怕美国疫情是很难有所缓解的,校园的封闭仍将持续下去。我忽然想起了T·S艾略特的诗句:
永远是一种可能性,
只存在于思索的世界里。
可能发生过的和已经发生过的,
指向一个目的始终是旨在现在。
脚步声在记忆中回响
沿了我们没有走过的那扇门
朝着我们从未打开过的那扇门,
进入玫瑰园。
也许在很多年后,等到杜克森林里的松鼠们又收获了满满一树洞的松果,我还会有机会找到一个安静的下午,穿过草地,慢慢走向Wong老师的办公室。
这一次,我一定和他好好聊聊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