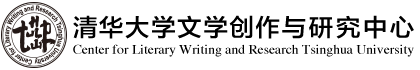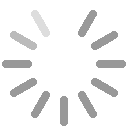稻禾深处(2018文学奖三等奖)
2018.11.25
作者:莫家楠,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
娘叫祥子回家吃晚饭时,祥子正坐在离家不远的田埂上看着夕阳下沉。太阳越来越大、越来越红,“真像一个柿子呀!”他想着。听到娘的声音后,祥子非常不情愿地回家了。
说是回家,但祥子一点都不认为那是他的家。祥子爹死得早,娘在半个月前带着祥子改嫁到离原来的家很远的新爹的家里,也就是现在祥子住的地方。
刚进屋,黄狗就迎上他,跟在他的脚边一直嗅,尾巴一摇一摇的。狗对他已经有点熟了,半个月前刚来的时候,狗一直冲着他和娘叫,他想捡起石子去打狗时,那个自己日后要叫做爹的男人就出来把狗赶走了:“小畜生,一边去!”想到这,祥子也学起了男人那时的语气,轻轻踢了狗一下,说:“小畜生,一边去!”狗轻吠了两声,朝屋外跑去了。
桌上摆的饭菜是水煮鱼和娘做的咸菜。那条鱼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祥子,祥子忍不住拿筷子戳了戳鱼的眼睛。
“哟,祥子,”男人笑着说,“想吃鱼吗?那是我今天刚去去田里捉的稻花鱼,可香了。”祥子想问啥叫稻花鱼,但话到嘴边却变成:“我不吃鱼,我只吃我娘做的咸菜。”然后捧起饭碗只顾埋头吃饭。
娘脸上挂不住,教训道:“鱼多好吃啊,明天我们就要送你去上学了,吃鱼补脑子,快吃!”
“我饱了,”祥子放下碗筷,“我已经吃完一碗饭了。还有,我也不想上学!”说着就跑出了这个家。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祥子抬头看天,原先的红太阳已经不见了,只有一个弯弯的银月挂在云端。祥子眯起眼睛,把灰色的云想象成眼睛、鼻子和嘴巴,再配上弯弯的月牙,他觉得整个天宇就像包公的脸。祥子站的土路被稻田包围,蛙声片片。
四周黑乎乎的,萤火虫打着小灯笼在水田上面轻悠悠地遨游。绿莹莹的萤火之中混进了一点红色的灯光。祥子小心翼翼地沿着田埂往灯光的方向走去。走近了,他发现那是从一所破败屋子里透出来的昏暗灯火。
“不会是鬼屋吧?”祥子有些害怕了。他想回去,但是一想到那个家,他就重新鼓起勇气,拍拍胸脯进去了。推门进去的那一刻,门缝里传来了嘎吱的响声。屋里只有两间房,外屋应该是个厨房,灶台上放着一个碗,碗里有松木片,它在寂寂燃烧着。这是当地人照明的方式。地上放置了一堆干稻草和一个板凳。空气湿漉漉的,有稻草的清香味,有青苔的霉腐味,也有一股烟草味。
祥子大失所望,气呼呼地踢了脚边的干稻草。这声音惊动到了里屋的人。那人出来,看了祥子一眼,赶忙低头护住稻草:“伢崽,这可使不得!”
那是个老人,头上围着一圈毛巾,那毛巾看得出来已经用了很久;他的两个眼窝深深地凹陷下去,镶嵌其中的两只眼睛浑浊无神;他的脊背弯曲,就像麦田里直不起腰的麦秆。由于灯火昏暗,他的其他五官全都隐没在黑色之中。他向祥子伸出枯枝般的手,喉咙里发出喑哑低沉的声音:“伢崽,要我教你做草鞋吗?”
祥子逃也似地离开了那里,往家的方向奔去。“真像一个僵尸。”他想。
祥子第二天还是去上学了。但他一节课都听不进去。他讨厌这里,讨厌这里湿漉漉的长着青苔的教室,讨厌老师浓重的少数民族口音,那种口音就像这里的糯米饭一样,黏黏的。祥子于是拿出本子,开始画画,画他黄土高坡上的家。
同桌的女生凑过来,好奇地看着祥子的画。女生的眼中透出惊奇的神色,问他:“哇,这是啥呀,怎么山坡上有这么多的洞洞?”祥子现出洋洋得意的样子,很为他的老家感到自豪:“这是我家,在黄土高原呢!那些洞洞就是门和窗。我们住的地方叫窑洞。”
“我们这也是高原呢,叫啥云贵高原……我记得我阿姊的课本上是这么说的。”小女孩儿怒力回想着课本上的话。
女孩名叫朵子,她和祥子很快就成了朋友。下课后,朵子拿出两个小背篓,带着祥子去自家田里捉鱼。碧油油的稻田连成一片,一望无际,水稻都已经吐了穗,白色的稻花颤颤地立在稻穗上。稻田里有几条人为的交错纵横的沟,这几条沟的存在,不仅方便了夏天开田捉鱼,而且在秋天割稻时能有个落脚之地。祥子和朵子就是在这几条沟中捉鱼。
祥子之前在黄土高原时倒是帮娘割过麦,但是他没碰过水也没下过田。他一板一眼地学着朵子的动作,挽起裤脚和衣袖,将背篓系在腰间,然后便赤脚下水了。水凉凉的,脚泡在里面很舒服,水底的淤泥柔软,祥子一踩就陷进去了,但稍微用些力就能继续前行。
祥子一开始很高兴这样的感觉,在水田里玩得不亦乐乎,完全忘记了要捉鱼的任务。直到有一条鱼不小心被朵子遗漏然后游到了祥子的两腿间,祥子才想起来要摸鱼。他两手伸进泥里,牢牢地抓住鱼。那鱼的力气可真大啊,一直想要摆脱出祥子的手掌,还溅了几滴泥在祥子的衣服和脸上。
祥子将鱼拿进背篓,自豪地说:“这可是我抓到的第一条鱼,我要把它养起来!”然后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问朵子:“朵子,啥叫稻花鱼啊?”朵子说稻田里的鱼几乎都是草鱼,因为它们养在稻田里,吃饱了稻花,肉里面有稻花的香味,所以叫稻花鱼。
“那我把其他鱼养在稻田里,它们吃饱了稻花,也能叫稻花鱼咯?”祥子问。
“也许吧……但我们这里大部分的鱼都是草鱼呢。”朵子有点回答不出这个问题。
傍晚时候,他们已经抓到了很多鱼,但是在朵子的建议之下他们放了一些鱼,只留下三只最大的和祥子捉到的第一条鱼。“那条鱼我送给你了。”朵子爽快的说。
他们一路上有说有笑地回到寨子。在经过寨口的风雨桥时,他们看到一群不怀好意的青年捡起一颗石子朝桥下的空水田里扔去。那颗石子扑通一声落在了一个佝偻的老人面前,溅起水花。祥子捂住嘴,他认出了那个老人就是头天晚上在破屋见到的那个。
“不去卖你的草鞋,在田里干嘛呢,张嘎老。”那几个青年笑着说,祥子知道“嘎老”是这里的方言,就是“老头”的意思。
在日光之下,祥子能看清老人的长相了。他瘦小且黑,沟壑纵横的脸上拼凑着丑陋的五官。老人咧开嘴笑,发黄的牙齿便露出来了,他说:“草鞋卖不出去了,我来田里捡螺蛳,寨口的张老板收呢……”
那几个青年不再理他,开始讨论晚上的行歌坐月要怎样讨女孩子的欢心;老人也继续埋头捡螺蛳。祥子问朵子那老头是什么人,朵子年纪也小,了解的也不多,只知道那老头没有什么亲人,一个人靠买草鞋为生。
因为自己抓到鱼了,娘和那个男人都很高兴,他们觉得这是祥子开始融入这里的一大表现,但是祥子却认为他们是因为晚上可以吃鱼而高兴。于是他找个一个小木桶把那条鱼养起来,放在自己的房间里,不让娘和那个男人给杀了做菜。
吃过晚饭,朵子来找祥子玩,她说想带祥子到寨子里四处走走。祥子说自己比较喜欢水,于是两个小孩子便踩着田埂到达河边,沿着河边一直走。因夏夜多蛇虫,他们就拿着木棒,敲打着路边的草丛,希望把蛇给惊跑,蛇没惊出来,倒是飞出来了许多打着绿色灯笼的萤火虫。
朵子突然想到每次自己要晚上出来玩时,阿妈哄吓自己的“变婆”的故事。“祥子,你听说过‘变婆’吗?”祥子摇摇头说没有。
这时走在前面的朵子突然转过头来,神神秘秘的:“小孩子啊,晚上千万不要一个人出门,否则会被变婆抓走吃掉!”
祥子撇撇嘴,表示不相信。
朵子说:“以前有一对姐弟要去外婆家,他们的妈妈就说:‘崽啊,牛屎路是通往外婆家的,猪屎路是通往变婆家的,你们千万不要走错啊。’这时候呢,门外的变婆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把牛屎路和猪屎路给换了……”朵子正说着呢,突然感觉到头上有什么东西在动。抬头一看,祥子正从自己头上拿下一只亮莹莹的萤火虫。“它停在了你的头上。你继续说。”祥子说。
朵子继续说下去,仿佛从来没有被打断。走着说着,逐渐听到了隐隐的歌声和琵琶声,那歌声如薄雾,袅袅地罩在寨子上方。那歌声越来越近,走近了才发现,歌声是从风雨桥那里传过来的。正巧二人有些累了,就在前面的风雨桥歇脚。
风雨桥的一边三五成群地坐着些姑娘,她们头上戴着银花,颈间戴着银项圈,腕间戴着银镯,打扮得很是漂亮。姑娘们在做着女工,含着秋波的眼却时不时瞟向对面坐着的一群青年。青年们不似姑娘们那般害羞,大大方方地看着她们,弹着手上的琵琶,给姑娘们唱情歌。一个男子唱歌,必有一个女子来和;又或者一个女子唱歌,必有一个男子来和。歌声绵长柔细,好似寨子中飘渺的青烟,又好似山中淙淙泉水从杉树林中流过。清朗的月亮挂在山头,洒下的月辉在河水中变成粼粼波光。
朵子解释说,这叫行歌坐月,青年们借此表达感情、寻觅良人。祥子听到这歌声,不免想起了家乡的梆子腔。人们敲打着梆子,用近乎嘶吼的声音喊出自己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还记得有一次割完麦,大家招待即将返程的麦客们,晚上便在戏台那里请人唱梆子戏。演员们下台之后,一个老人在台上拉着二胡,用粗犷悲怆的声音吼出秦腔,祥子记得,老人唱完之后微张着嘴仰着头望着天空,有两行浊泪从他眼角流下。
想到这里,祥子不知不觉也哭了。突然他感觉到有一只粗糙的手帮自己捻泪:“伢崽,莫哭哩。”是那个做草鞋的老人。祥子之前只顾着和朵子说话,并没有注意到自己旁边坐着这位老人。“伢崽,光景这么好,哭啥咧?”那老人又笑着说。
祥子突然不觉得老人可怖了,反倒觉得他很亲切。祥子说自己有点想家了,所以才哭。老人摸摸他的头,说:“莫哭莫哭。你家一定离这很远吧?家里有啥牵挂的人吗?”
祥子说他家离这里真的很远很远,虽然家里没人了,但他还是想回去。老人心疼地说:“这么小就离家这么远,真叫人心疼哩。小娃娃想家正常嘛,难过啊,不适应啊,很多很多委屈,是不是?嘎老我理解的。但这些事儿啊慢慢就会过去的,你会发现这里的人很好的,时间一长你就会习惯这里甚至是喜欢上这里。而且,你长大就可以回老家看看啊,你的阿妈也还在你身边,伢崽你还有很多机会哩。”
伢崽平稳了情绪,问张嘎老为什么在年轻人聚会的地方乘凉。老人笑笑:“哈哈,老人就不能看年轻人谈情说爱啊?每次看到他们,我就想起那时候我和我婆娘就是这样在一起的,可惜她……”
祥子这才知道,张嘎老原来是有妻子的,但是那一次难产,大人小孩儿都没了。张嘎老从此就一个人守着那个老屋。“有亲人的地方就是家,那么好的阿爸阿妈就在你身边,娃崽你要珍惜哩。”祥子离去时老人这样说。
回去的路上,朵子有些兴奋又有些难过:“我刚才看见我阿姊和一个哥哥交换了东西,我想她很快就会嫁出去了,有点舍不得她呢。”祥子应了她一下,脑子里却一直想着老人那句话。
第二天祥子起床时,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娘跟着寨子里的其他女人去采茶了,而新爹则带着黄狗去山上砍柴了。
祥子扒拉了几口油茶,就去约朵子一起上学。上学路上,他看到张嘎老背着一个装满草鞋的大背篓佝偻着身子,一手拄着棍,一手扶着身后的背篓,蹒跚地朝寨外走去。
祥子一放学就跑到了张嘎老家。门并没有锁,祥子推门进去,里面没人。那天晚上看得不真切的景象现在清晰地展现在他面前。外屋的器具很简单,地上仍是散乱着稻草,祥子这时候明白了这是编草鞋用的。一个并不是很结实的土灶台上静静躺着一双碗筷。房子的四壁很是破败,木板和木板之间的缝隙很大,能投进来许多光,也投进了风风雨雨。祥子进到里屋,里面只有一张床,床上铺着稻草,可以增加舒适度。祥子躺在床上等着张嘎老的到来,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他是被张嘎老叫醒的。祥子说自己想来找他玩。“我可以教你编草鞋啊。”老人说。老人放下背篓,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教祥子如何编草鞋。老人的手很灵巧,不仅会编织草鞋,还会编织草帽、草枪、草风铃等小玩意儿。“阿公,这些都是你自个儿想出来的吗?”祥子问。
“对啊,编久了就自然能琢磨出新花样了。每次赶场,我都会拿我的草鞋到场里卖,但现在镇上都有橡胶鞋卖了,没几个人要买我的草鞋。我就想着编一些小玩意儿,城里的小孩子也挺喜欢的,也能赚口饭吃。”
“那你今天早上是去赶场吗?”
“是啊,平时天没亮就走了,今天腿难受起晚咯,所以才能让你这个学生娃子看见。”老人笑呵呵地说。
老人看了一眼天边,红红的太阳已经和远山相切了。老人说:“太阳鸟已经飞到西边了,伢崽,你赶紧回去吧,你阿爸阿妈该担心你了。”
祥子还没玩够,不过还是听话地收拾了自已的东西,一边把玩草枪一边回家。
娘还没回来,那个男人正在家中做饭。看到祥子,男人从灶台的烟雾中抬起头来,咧开嘴笑了:“怎么才回家呀,是不是和同伴去玩了?”然后他从墙上拿下来一个小背篓递给祥子,对祥子说:“我从山上采的,可好吃了。”那里面是一些树莓。
祥子接过来,看了男人一眼,道了声谢。男人宽厚的手掌摸了摸祥子的头,说:“我都是你阿爸了,谢啥谢。”他的眼神突然黯淡了下去,放下了手,说:“你要是不愿意叫阿爸,叫叔也行。”然后男人转身,回到灶台前继续做饭。
娘从茶山回来了,男人迎上去:“今天采茶怎么样了?”娘放下采茶的背篓,笑着说:“头一回采茶,速度没人家快,但也换得了一些小钱。”
今晚的菜是男人做的,但他居然做了咸菜:“你娘说你喜欢吃咸菜,这是前几天我腌的,你尝尝味道咋样?我很会腌酸菜的,我想腌咸菜应该也差不多。”
祥子吃了一口,男人很期待地看着祥子,两只手局促地在衣前相握着。味道其实还可以,但比不上娘做的,也没有家乡的感觉。若是几天前,祥子可能吃都不会吃:“你腌的咋能比得上我娘腌的。”但是这次,他却说:“嗯嗯,味道不错呢。”虽然说出这句话时,他很别扭。
时间如流水般淌过,转眼间已到初秋。稻田里的稻谷青黄相接,再过十把天便可收割。人们到稻田里放水,把鱼都捉来,留下干田。只要再经过太阳十几天的灼烧,田泥干燥龟裂,人们就可以站在上面收割稻谷了。
祥子提着鱼篓跟着新爹到田里捉鱼。新爹说,以手掌为标准,比手掌大的鱼放在大的鱼篓里,比手掌小的鱼苗就放在小的鱼篓里。鱼苗先不吃,转移到鱼塘里先养着。由于水都被放走了,大鱼们已无处遁形,在淤泥里挣扎着,祥子很容易就把鱼都给捉光了。
祥子看着一大箩筐的鱼,不禁担心道:“叔,这么多鱼,咱家吃不完啊。”祥子现在叫那个男人为“叔”。男人笑笑说:“没得事,回去把这些鱼腌了,至少能吃小半年。”
祥子坐在田埂上,看着青青黄黄的田野:“怎么没看到张嘎老来放水捉鱼?”
男人直起腰来:“他家只有一块薄田,而且年纪大了,田活要做的事又多,老人家折腾不起的。前两年他还种田呢,结果割稻的时候腰闪了,没钱治,在床上躺了好几天,没死已经是老天爷的眷顾了。但他从此也落下了病根,再没有种过田。他平时做草鞋的稻草都是和寨上的其他人要的。婆娘娃崽还去世得这么早,诶,苦命人啊。”
祥子看向男人,男人动动嘴唇似乎还想要说什么,但最终仍是叹了口气继续干活。
晚饭桌上出现了酸汤鱼。祥子夹起一块肉,小心翼翼地避开鱼刺。但是每次他都是吃一半留一半,这样他的碗中剩下了很多还没有吃完的鱼。娘忍不住责骂祥子浪费粮食。祥子说自己觉得好吃,想留着待会儿饿了再吃。晚饭后,祥子端着剩下的那碗酸汤鱼蹑手蹑脚地走出家门,敲开了张嘎老家的门。“伢崽,是你啊。”老人布满褶皱的脸上扬起一个笑容。
“阿公,我送酸汤鱼给你。这是我……我阿爸做的鱼,寨上的人都说他做的酸汤鱼最好吃了。”祥子捧着碗,“你吃吧,等凉了就不好吃了。”
老人接过鱼汤,那诱人的香味像毛毛虫一样钻进了他的鼻孔。祥子拿出筷子递给老人,让对方坐下来:“阿公,你快吃吧。”
老人颤抖的手接过筷子,时而看看祥子,时而看向酸汤鱼,却迟迟没有落筷。祥子急了:“阿公,你快吃呀,都快凉了。”老人黝黑的脸上突然划过一滴泪,他连忙拿手去擦,然后说:“伢崽啊,你学生娃子还要长身体,你吃吧。别拿给我一个嘎老,糟蹋了这么好的粮食。”说着就把鱼递给祥子。
祥子说自己已经吃过了,老人才犹犹豫豫地拿回碗。他夹起最好的一块肉,递到祥子嘴边:“来,伢崽,你吃这块。”祥子吃下了那一块,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吃了:“我再吃的话,你就没有来了。”老人只好顺他的意,吃起了鱼肉。明明一碗再简单不过的菜,老人却细嚼慢咽,生怕自己一会儿就吃完了。
老人放下碗筷,握住祥子的手。祥子能感觉到老人粗糙厚实又温暖的手心将他的小拳头稳稳包住。
“没想到我这个糟嘎老还有你这个伢崽挂念。”一滴泪顺着老人脸上的沟壑流下,“要是我的女儿没死的话,我的外孙崽也跟你差不多大了。”
祥子的思绪飘到了外面,张耳细听,蛙声已经没了。
祥子走到家门口时,男人出现了。他看着祥子手中空空的碗:“你莫告诉我,你边散步边吃这碗鱼。”祥子埋下头去。男人走过来,拍拍他的肩:“你想把鱼留给张嘎老就和我们说,我们肯定不会阻止的嘛。你不了解我难道还不了解你娘吗?”祥子抬起头看着男人:“对不起。”男人笑了:“不用说对不起,我很高兴你是个心善的娃。”
自从那晚送了酸汤鱼之后,祥子就再也没有去张嘎老家。祥子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自从老人握着他的手在他面前哭泣后,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在他心底滋生。那种感觉拉开了他和老人的距离,他不知道如何面对老人了。每当他想去找老人,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老人老泪纵横的脸,于是他就失去了勇气。可能他只是单纯地不喜欢有人在自己面前哭,不喜欢有人握住自己的手。但是,如果是朵子在哭,是朵子握住自己的手,他估计他自己是没有这样的感觉的。又或许,他不习惯长辈的温情和软弱吧,在那种情况下,他会变得无所适从、局促不安,不知道该作何反应才是对的。祥子从小和娘生活在一起,他不晓得如何与其他大人相处。他一直以为大人是威严且坚强的,当他见过了张嘎老流泪后,他就很难以一种平常心面对张嘎老了。于是,他选择了逃避:有时候,他会去找朵子玩;有时候,他会和男人去砍柴。
秋意渐渐浓了,秋风一吹,树林就变得五颜六色起来,红的、橙的、黄的、绿的,拼凑在一起很是好看。山林匍匐在寨子的后方,像一只色彩斑斓的老虎。
祥子到山林砍柴时,偶尔会遇到背着背篓蹒跚前进的张嘎老。祥子看到他,就会找个地方躲起来。老人的步履颤颤巍巍,走了没几步便会歇一下,然后他捡起松枝当做拐棍继续往前。等老人走远了,祥子就出来,他看着老人远去的背影,突然很想哭。
祥子闷闷不乐地回到家,坐在床沿上看着桶的鱼游来游去。朵子来了,她告诉祥子,她的姊姊今晚就要出嫁了,对象就是那晚对歌的青年。
“晚上那么黑,为啥要在晚上结婚,不怕变婆吗?”祥子问。
“今晚只是抢婚,过几天再正式举行婚礼。”朵子拉着祥子往楼下跑,“今晚你来我家吃饭吧,你阿妈也过来呢。”
祥子到了朵子家,只见到盛装打扮的新娘,没看到新郎。朵子拉着祥子到新娘子的房间,里面挤着一群年轻的姑娘。她们看到祥子都笑起来了,毫不吝啬地展示她们的大白牙:“小伢崽也是男的,咋能随便进新娘子的房间呢?”祥子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她们笑得更厉害了:“还会害羞哩!”
到了很晚很晚的时候,只见新郎领着一群青年气势汹汹地来到新娘家门口,冲着楼上叫道:“快叫新娘子下来,否则我们就上去了哩!”
那群姑娘从房间里出来,朝着小伙子们喊道:“小伙子们,瞧瞧我们谁是新娘啊?”然后便一哄而笑。祥子当时想,这群姑娘可真是爱笑啊。
青年们受了戏弄,纷纷进屋寻找新娘,脸上却是笑嘻嘻的。姑娘们拿着篾子、笤帚在青年们的身上狠狠敲打,让他们知道迎娶新娘并没有那么容易。经过一番折腾,小伙子们虽然进了房间,但也狼狈至极。祥子和朵子躲在房间的角落看热闹,生怕误伤了自己。一个小伙子连忙背起新娘往外跑,另一个青年则脱了新娘脚上的绑着红丝带的草鞋。“草鞋,那是张嘎老做的草鞋吗?”祥子有些恍惚。就在这时,其他的青年马上围在新娘身边,怕姑娘们把新娘抢走,也怕伤到新娘。小伙子们背着新娘远去,向身后的姑娘们发出胜利的叫喊声。
祥子问:“他们要把新娘带到哪里去?”
朵子说:“带到新郎家去住半个月,半个月之后才回来正式求亲呢。诶,我会想我阿姊的。”
祥子想到了那个草鞋,说:“新娘子脚上的草鞋是谁做的啊?”
“那个啊,那是张嘎老做的,抢婚的时候新娘子要穿系着红绸的草鞋。”朵子说。祥子转过身,撑着两肘看着月亮,突然发觉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去看张嘎老了。
毒日悬在天上,晒得金黄的稻谷都要生烟。金黄稻海里藏着半裸的汉子们,他们在田间割稻,黝黑的上身流着汗,油亮亮的。祥子从家中带来一壶水拿给割稻的新爹,然后自己也加入割稻的队伍。但男人怕祥子中暑,就催促他回去:“祥子,这太热了,你回家歇歇,等到太阳下山的时候你再来。”
等到太阳与远山相切时,祥子披着蜜色的夕阳余晖回到了稻田。农人们已陆续归去,有人驾着牛车驮稻谷,优哉游哉地慢慢行走。今天是收稻谷的最后一天,田野变得光秃秃,只留一截截稻茬,但还能闻到那残留的稻谷香味和泥土清香。男人把稻草捆成一个草垛,稳稳地扎在稻田中央。有人在田野里烧秸秆,青色的烟升上天空,一些孩子在翻飞的秸秆灰屑中玩耍。
祥子和男人一人扛着一袋稻米回到寨上,远远地就瞧见了袅袅炊烟。男人像想起了什么,扭过头来问祥子:“你娘煮饭做菜了吗?叫你娘多做一些好吃的!今年的稻谷收完了,今晚寨上摆长桌宴,大家一起吃东西!”
人们从家中拿出桌子板凳,一张接着一张地摆在道路上,然后拿出自己家中的食物。一个月前入坛的腌鱼已经腌熟了,男人拿出几条腌鱼放在长桌上:“大家都来尝尝我家的腌鱼,可好吃了!”
突然有人牵着一头戴红花的牛从路中间走过,大声叫道:“今天请乡亲们吃牛肉!”人们纷纷鼓掌欢呼。祥子跟随着人群到田野上看杀牛。他拨开人群,看到几个年轻人制伏住焦躁挣扎的牛,一个老人拿着一把斧头上前来,往牛的脑袋上一击,祥子连忙蒙住眼睛。等睁开眼,那牛躺在地上已经不动弹了,地上鲜血四溅。那个杀牛的老人转过身来,是张嘎老。他欣喜地朝人群挥手,突然他看见了祥子,眼中的光彩黯淡下去,伤感代替了欣喜。但他马上恢复了欣喜神色,朝祥子挥手,祥子看到这一幕便退到人海中去。老人失落地走到角落里,只留下几个后生将死掉的牛开膛破肚。
吃饭时每桌都分到了一小碗牛肉,牛肉很快就被一扫而光。祥子意犹未尽地看着空空的小碗,这时突然感觉有人拍自己的肩膀。张嘎老的笑脸映入眼帘,他端着一小碗牛肉说:“嘎老我帮忙杀牛,也有一份牛肉哩!来,伢崽,你尝尝。”
祥子说不用了。张嘎老急了:“我一个嘎老牙不好,吃不完的!”这时候祥子的娘说话了:“老人家,你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吧,我去添个板凳。”
张嘎老坐在祥子身边,男人给他倒了一碗米酒。男人说:“嘎老,你年纪这么大了,以后有人再叫你去杀牛,你不要去了。”
张嘎老端起米酒噙了一口:“要去的,除了我寨里也没得哪个可以杀牛了。帮大家一个忙,我自己也有一碗牛肉哩。”
宴会结束时,祥子一边擦桌子一边问男人:“叔,为啥要张阿公杀牛,其他年轻人不可以吗?”
男人说:“牛是农人的宝,特别在咱这儿,山路崎岖,牛就是命根子!如果杀了牛,那么自己的亲人就会遭报应。所以毙命的那一锤,必须要一个无妻儿的孤老来动手。”他叹了口气,“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为了报答,最好的那块牛肉要留给杀牛的老人。”
桌椅收拾完毕了,男人拉住祥子:“张嘎老没有孩子,所以对小孩子很有感情。我看你之前和他关系那样好,我也觉得很欣慰。我知道你是个心善的娃,但我不知道为啥最近你不像以前那样和他亲近了。他和咱们无亲无故的却对你那么好,咱也不能视而不见啊,你说对不对?”男人读过几年书,有时说话和其他农人不一样。
祥子回到自己的房间,秋凉随着月光送入房中。祥子躺在床上,久久睡不着。
祥子又像往常一样去找老人玩儿,老人很高兴。老人说:“明天我去市集卖草鞋,你想不想一起去?”祥子愉快地答应了,这么久了,他还从来没有到市集上呢。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沿着小路翻山越岭到市集去。说是小路,其实只是人踩出的一条痕迹罢了。翻越了几座山头儿,他们终于能瞧见市集的样子。下坡的时候,祥子看着市集入了迷,脚下一滑就快摔下坡去,老人右手紧紧拉着他,左手顺势抓住一把野草借力。祥子站稳之后,发现老人的左手被草划破了。红色的血在黑色的皮肤上蜿蜒。
“伢崽,我没得事的,上一些草药就可以了,你莫要担心。”老人用没受伤的右手拍拍祥子的肩膀,俯下身摘下几片叶子,放入口中咀嚼然后涂抹在伤口上。
到了市集,老人选一块地方坐下,将草鞋摆放在面前。祥子的心思并不在草鞋上,市集里的商品不多,但足以让他眼花缭乱。有吃的,用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其中他最喜欢的就是不远处的冰糖葫芦。但他没跟老人说,他知道老人没啥钱。
人群熙熙攘攘,老人时而用汉语时而用侗语招呼过往的行人,但没人愿意买。偶有一两个驻足的,看过之后就走了。时间逼近正午,老人没卖出去一件东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冰糖葫芦大受欢迎,只剩下几根了。虽然已经是秋天了,但正午的日头依然毒辣。太阳晃得祥子眼前出现彩色的圆圈,冰糖葫芦变得模糊起来;耳朵充斥着嗡嗡的声音,中间夹杂着老人虚弱的叫卖声。黑暗如大山倾倒,祥子昏了过去。
祥子在一棵大树下醒来,光斑如蝴蝶一般停在他红红的脸蛋上。男人和老人的脸出现在他面前。“祥子,你好点了吗?”男人上前关切地问道。
祥子晕倒之后,张嘎老手足无措,大声叫喊,这叫声把刚好也在赶集的男人引了过去。幸好人群里有懂医的,说祥子只是中暑,男人便抱着祥子到树下休息。
张嘎老像是对男人说,又像是对祥子说:“都是嘎老我不好,不该在这么热的天还把伢崽带出来。”他的眼睛瘪下去,带着愧疚和担心的神色。
但祥子的注意力明显被男人吸引了,他并没有回答张嘎老而是问男人:“叔,你咋也在这儿?”
男人恢复了笑脸,举起一个白色的口袋:“怕你想念面食了,我就去买了点儿面粉。回头啊,叫你娘给你做点好吃的——她比我会做。”
祥子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但为了避开日头,三人打算先在树下歇一会儿再回去。张嘎老的草鞋一双也没卖出去。卖冰糖葫芦的地方已经没人了,想是已经卖完了,祥子失落地低下头。老人愧疚地想拍拍祥子的肩膀,但最终还是收回了手。
回到寨上,男人请张嘎老到家中吃晚饭,但他拒绝了。他在寨口目送着祥子和男人回家,直到人影消失在拐角之后,张嘎老眼中的烛火灭了,他背着和早上一样满当当的背篓,一步一步回到他孤零零的老屋。和他一样孤零零的老屋。
五天后,又一个赶集日。早上天空还蓝盈盈的,下午乌云却滚滚而来。祥子一家人赶忙去收正在晒太阳的谷子。收齐才没两分钟,雨就簌簌地下了。这里秋天的雨不大,但凉而绵长。它不像夏雨哗啦啦一阵就过去了,有时候一下就是一两天,雨水过后,天气也凉了。这里山路崎岖,土质疏松,下暴雨易滑坡,哪怕是中小雨,山间小道也是湿滑难走。男人一脸愁容:“那些赶集还没回来的人怎么办啊!”
到了晚上,雨还没停,丝丝凉风倒是起了。祥子从床角扯了被子过来,不再像前几日那样不盖被子了。他躺在床上,突然想起张嘎老:“张阿公不会也去赶集了吧?”但他最终仍是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夜风把窗扇弄得咔咔作响。
第二天早上,几个年轻人在通往市集的那座山林里找到了张嘎老的尸体。他背着背篓蜷缩着躺在草丛里,两手抱着胸,头下枕着一块满是血污的大石头,他黑色的皮肤和黑色的衣服上交错着泥水和刮痕。人们猜测应是前一天赶集回来时他脚下一滑,便滚进了草木深处,后脑勺撞上了大石头,因此送了命。人们叹息着,打算将他殓了。他蜷缩的身子被打开时,人们看见他双手怀抱着的是一根冰糖葫芦。它的糖皮已经化了,随着衣服的褶皱流淌下来,就像一行在流血的泪。
没人知道为什么,只有一个小男孩在那一刻扑向尸体大哭起来。一个男人面色凝重地走向前来,将手放在男孩一起一伏的肩膀上。蒙蒙烟雨包裹着他们,肃穆而阴沉。
晚上,雨仍然没停,夹杂着风吹打瓦片。房间木桶里的那条鱼还在悠闲地游来游去,偶尔溅起来的水花声在这个静悄悄的房间里显得格外突兀。祥子站在窗口,眼中蓄着泪看向外头。黑色的杉树林像一头蛰伏的巨兽。穿越雨点而来的低低声响,不知是风吹树林的声音,还是谁的呜咽。
感谢莫家楠对本文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