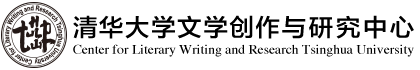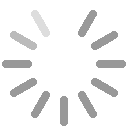清华文学研究 | 解志熙:《论语》疑难句解读(上)
2020.08.07
“清华文学研究”栏目旨在推介清华学人在文学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促进学术交流。
小 引
《论语》难得地保持了孔子当日与弟子等的言谈,大多平易近人、亲切如话,至今读来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很少滞涩难解之处,比其他子书都好懂些。但《论语》也别有所难——有些语录记载过简,言说线索不甚明瞭、语境不很清楚,加之传统训诂缺乏语法、语境意识,不免望文生训或曲说求通之处,所以平易近人的《论语》仍有些语句长期得不到恰当理解。很久以来我就发觉《论语》里的有些话,诸家所断所解扞格难通,或者不无误断误解。间尝也暗暗自求解断,虽然不敢自必必是,但写出来供读者参考并求正于方家,亦无不可吧?
这里就挑出《论语》的六个疑难句略作讨论。下面先列《论语》原句,次述通行注本的注解,再略说自己的意见。旧注以何晏《论语集解》的皇疏本和邢疏本、朱子《四书章句集注》里的《论语集注》和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为代表。《论语集注》是魏何晏等注,有梁皇侃疏、北宋邢昺疏。皇疏保存汉魏旧注最多,中土早已失传,乾隆时从日本回流中国,有“知不足斋丛书”本;邢疏节录皇疏加上自己的发挥,因入“十三经注疏”而广泛流行;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本《论语集注》代表了理学家的研究成就,是元明清的主导性读本;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是清代汉学的典范成果,流行最广。近人注疏以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杨树达的《论语疏证》、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钱穆的《论语新解》为代表。《论语集释》和《论语疏证》都撰于抗战时期,前者汇集古训加以辨析,是集大成的训诂之作,后者以史证文,诚如陈寅恪序之所言:“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开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斟酌旧注而能祛除古人对“经”的迷信,恢复《论语》之师生间自然问答的本来面目,是当代流传最广的注本。钱穆的《论语新解》折中诸说、简明得体。以上注本代表了古今训读《论语》的成果,各书版次甚多。下引1.《论语义疏》(皇疏)、2.《论语注疏》(邢疏),都用“四部要籍注疏丛刊”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3.《论语集注》(《四书章句集注》)用“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4.《论语正义》用“清人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5.《论语集释》用中华书局2017年版,6.《论语疏证》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7.《论语译注》用是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8.《论语新解》用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为免繁琐,下引只夹注书的序码和页码如(1-221)即《论语义疏》第221页。采及其他古人和时贤之论则出脚注。
1、“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如何断解?
“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出自《学而》篇,另见《子罕》篇。“无”又作“毋”。
从古至今对此句的句读或断句都是:“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可谓两千年一以贯之,从来无人怀疑。解释的纷歧也因此而生——由于把“己者”断属上文、与“无友不如”连读为“无友不如己者”,于是原本不难解读的文义,反而横生枝节、纷纭多歧。
直至宋代的旧注都围绕着“忠信”这个要件解读交友之道,算是没有偏离中心。皇疏谓:“又忠信为心,百行之主也。云‘无友不如己者’者,又明凡结交取友必令胜己,胜己则己有日所益之义,不得友不如己,友不如己则己有日损。故云‘无友不如己者’。或问曰:若人皆慕胜己为友,则胜己者岂友我耶?或通云:择友必以忠信者为主,不取忠信不如己者耳,不论余才也。或通云:敌则为友,不取不敌者也。蔡谟云:本言同志为友,此章所言谓慕其志而思与之同,不谓自然同也。夫上同乎胜己,所以进也,下同乎不如己,所以退也。闳夭、四贤上慕文王,故四友是四贤上同心于文王,非文王下同于四贤也。然则求友之道,固当见贤思齐,同志于胜己,所以进德修业,成天下之亶亶也。今言敌则为友,此直自论才同德等而相亲友耳,非夫子劝教之本旨也。若如所云,则直谅多闻之益、便辟善柔之诫,奚所施也?”(1—162-163)应该说,皇疏差不多把各种可能的解释都说到了,且引东晋蔡谟的《论语蔡氏注》文,则表明比较推重“必友胜己者”说。邢疏保存了一点汉代旧注:“郑曰:主,亲也;惮,难也。”其疏乃谓:“‘主忠信’者,主犹亲也,言凡所亲狎者皆须有忠信者也。‘无友不如己者’,言无得以忠信不如己者为友也。‘过则勿惮改’者,勿,无也,惮,又难也,言人谁无过,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故有过无得难于改也。”(2—312)邢疏显然把“忠信”视为择友的充要条件。朱子《论语集注》之解是:“主忠信,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故学者必以是为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诚则无物,且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者,人心也。若无忠信,岂复有物乎?’无友不如己者,无、毋通,禁止辞也。友所以辅仁,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过则勿惮改,勿,亦禁止之辞。惮,畏难也。自治不勇,则恶日长,故有过当速改,不可畏难而苟安也。程子曰:‘学问之道无他也,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当如是也。’游氏(程门高弟游酢——引者按)曰:‘君子之道,以威重为质,而学以成之。学之道,必以忠信为主,而以胜己者辅之。然或吝于改过,则终无以入德,而贤者亦未必乐告以善道,故以过勿惮改终焉。”(3—50)又,朱子在《四书或问》中对此章有更详细的讨论,并附苏轼的观点:“苏氏曰:世之陋者乐以不己若者为友,则自足而日损,故以此戒之,是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如必胜己而后友,则胜己者亦必不吾友矣。”朱子认为“苏氏之说,盖得其略。”[1]。
朱子可能没有想到,他附录的东坡之说会惹出无穷的麻烦。元人陈天祥的《四书辨疑》就批评朱子道:“注文本通,引东坡一说致有难明之义。”(转引自5—45)的确,截止朱子的集注基本上都坚持“无友不如”之不如的,就是承前省的“忠信”,而“忠信”乃正是交友的基本道德标准,“言无得以忠信不如己者为友也”,这至少紧贴“忠信”、语义较通的。只是由于前人顺着辞气把“勿友不如”与“己者”连读一气,如此多出了“己者”,也就预埋下了问题。如前所述,皇疏早已揭示出“胜己”说的矛盾——“若人皆慕胜己为友,则胜己者岂友我耶?”由于皇疏在南宋后失传,皇侃此说遂被淹没,但北宋的苏东坡和程门高弟游酢等应该都还读过皇疏的,游酢并特别推重“胜己”说,可是富有才辨的苏东坡对程门之说不以为然,乃不客气地质疑道:“世之陋者乐以不己若者为友,则自足而日损,故以此戒之,是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如必胜己而后友,则胜己者亦必不吾友矣。”东坡意谓孔子只是有鉴于世上的一些浅陋之人喜欢交接一些不如己的朋友,由此自足自封而德性日损,所以夫子乃以“无友不如己者”一句话提点人应求友于先进、庶几更有助于进德辅仁,所以东坡希望学者不必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刻意求深解读此句,纠缠于友人必须如何“胜己”,故此他才警告说“如必胜己而后友,则胜己者亦必不吾友矣。”朱子显然体认到东坡对刻意求深之解的批评旨在维护夫子的苦心,所以肯认“苏氏之说,盖得其略。”只因东坡的大名,他继皇疏之后再次揭出“如必胜己而后友,则胜己者亦必不吾友矣”的悖论,格外引人瞩目——其实,只要把“无友不如”与“己者”连读为一句,这悖论就存在,不论解者在“无友不如”与“己者”间加上什么德性条目,都无法祛除其斤斤于优劣比较的交友观之违和感。
正惟如此,南宋之后的学者大多偏离了“忠信”这个要件,而纷纷为苏东坡所揭示的悖论弥缝,却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人己道德优劣的种种锱铢必较中。常见的解读套路是寻求己与友在德性上的均衡,以免“不如己”或“胜己”的偏颇,但其实难得其平。因为完全的德性均衡很难考量也极其难为,并且按照“见贤思齐”的进德逻辑,可交之友也只能是“胜己”之人。如此一来,诚如清人黄式三《论语后案》所感叹的:“信如是计较优劣,既无问寡问不能之虚衷,复乏善与人同之大度,且己劣视人,人亦劣视己,安得优于己者而友之乎?朱子弥缝游说甚费辞。”(转引自5—45)但人们还是不得不继续弥缝。如元陈天祥《论语辨疑》不满朱子引东坡之说,以为“学者往往以此为疑,故不得不辨。‘如’字不可作‘胜’字说。如,似也。……不如己、如己、胜己凡三等。不如己者,下于己者也。如己者,与己相似,均齐者也。胜己者,上于己者也。如己者德同道合,自然相友。孟子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此皆友其如己者也。如己者友之,胜于己者己当师之,何可望其为友耶?如己与胜己既有分别,学者于此可无疑矣。”(转引自5—45)如此刻意求“友其如己者”之均衡,其实难乎其难。黄式三的《论语后按》则谓:“不如己者,不类乎己,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陆子静曰:‘人之技能有优劣,德器有大小,不必齐也。至于趋向之大端,则不可以有二。同此则是,异此则非。’陆说是也。依旧注,承‘主忠信’反言之。不如己,谓不忠不信而违于道者也。义亦通。总注游氏说以不如己为不及己。信如是计较优劣,既无问寡问不能之虚衷,复乏善与人同之大度,且己劣视人,人亦劣视己,安得优于己者而友之乎?朱子弥缝游说甚费辞。”(转引自5—45)其实,黄式三所肯定的陆子静之说,也不过用己与友“趋向之大端”的均衡来掩饰不能配德均齐的问题,所以仍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弥缝之谈。刘宝楠《论语正义》则引曾子和周公之言为孔子作证:“曾子《制言中》:‘吾不仁其人,虽独也,吾弗亲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与处,损我者也。与吾等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吾所与处者,必贤于我。’由曾子及周公言观之,则不如己者即不仁之人,夫子不欲深斥,故只言不如己者而已。”这也是有意含糊其词之谈,且所引曾子之言以仁代替忠信,周公之言则出自《吕氏春秋》,当是后人拟构,不足为证的。现代学者杨树达《论语疏证》则在“无友不如己者”后面加按语云:“友谓求结纳交也,纳交于胜己者,则可以进德辅仁。不如己之人而求与之交,无谓也。至不如我者以我为胜彼而求与我为交,则义不得拒也。”(6—15)杨树达对如不如己的问题予以人我不同的分疏,以为我求友必“纳交于胜己者,则可以进德辅仁”,至于“不如我者以我为胜彼而求与我为交,则义不得拒也”。如此人我分疏并不能解决苏东坡所揭示的矛盾。今人杨伯峻《论语译注》将此句径直译为:“要以忠和信两种道德为主。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有了过错,就不要怕改正。”随后的注释是:“主忠信——《颜渊篇》也说,‘主忠信,徙义,崇德也。’可见‘忠信’是道德。无友不如己者——古今人对这一句发生不少怀疑,因而有一些不同的解释,译文只就字面译出。”(7—6)杨伯峻显然深感此句难以理顺,故此不愿强为之说,只照字面译为“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这至少不失诚实的态度。钱穆的《论语新解》也老实按照“无友不如己者”的字面意义,解为“与不如己者为友,无益有损”,但他显然有感于旧注在如与不如上难得其平的纠结,所以提醒读者说:“窃谓此章决非教人计量所友之高下优劣,而定择友条件。孔子之教,多直指人心。苟我心常能见人之胜己而友之,即易得友,又能获友谊之益。人有喜与不如己者为友之心,此则大可戒。说《论语》者多异解,学者当自知审择,从异解中善求胜义,则见识自可日进。”(8—8)看得出来,钱穆面对这个异解多端、难以解通的句子,也有点无可奈何,只能要求读者“善求胜义”了。
当代学者南怀瑾和李泽厚则另有别出心裁的新解。南怀瑾的《论语别裁》讲到此句,先批评“朱文正公及有些后儒们,都该打屁股三百板,乱注乱解错了”,因为“无友不如己者”这句话,“照他们的解释,交朋友不要交到不如我们的。这句话问题来了,他们怎么解释呢?‘至少学问道德要比我们好的朋友。’那完了,司马迁、司马光这些大学问家,不知道该交谁了。……假如孔子是这样讲,那孔子是势利小人,该打屁股。照宋儒的解释,那下面的‘过则勿惮改’又怎么说呢?又怎么上下文连接起来呢?”然后南怀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么,‘无友不如己者’,是讲什么呢?是说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不要认为任何一个人不如自己。上一句(“上一句”指“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引者按)是自重,下一句是尊重人家。我们既要自尊,同时要尊重每个人的自尊心,‘无友不如己者’,不要认为你的朋友不如你,没有一个朋友是不如你,世界上的人,聪明智慧大约相差不多,……所以,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人与人相交,各有各的长处,他这一点不对,另一点会使对的。……‘无友不如己者’,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我们应该用其长而舍其短,所以‘过则勿惮改’,因为看到了每一个人的长处,发现自己的缺点,那么不要怕改过,这就是真学问。”[2]李泽厚在《论语今读》里把“无友不如己者”译为“没有不如自己的朋友”,在后面的“记”里则解释说:“‘无友不如己者’,作自己应看到朋友的长处解,即别人总有优于自己的地方,并非真正不去交结不如自己的朋友,或所交朋友都超过自己。如是后者,在现实上不可能,在逻辑上作为普遍原则,任何人将不可能有朋友。所以它只是一种劝勉之辞。”并发挥说:“‘忠’、‘信’又是两个重要范畴,既关系乎情感,又塑造乎人格。但其位置仍次于‘仁’、‘孝’。”[3]按,南怀瑾的书1976年就在台湾出版、1990年复在大陆出版,李泽厚应当是看过《论语别裁》、接受了南怀瑾的看法,只是在《论语今读》里没有说明。南怀瑾和李泽厚都是脑子聪明的人,他们别出心裁地把“无友不如己者”解读成“不要认为你的朋友不如你,没有一个朋友是不如你”或“作自己应看到朋友的长处解,别人总有优于自己的地方”。这乍一看似乎意味更长,但问题是“无友不如己者”中的“友”,从古汉语来说只能是动词而不可能是名词,则所谓“没有朋友不如自己”就成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想当然之论。
应该说,所有这些勉强牵强、曲折缠绕的解读,都源于对“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的断句——自汉迄今一直把“己者”断属上一句,整段话便被点读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于是,皇疏所谓“若人皆慕胜己为友,则胜己者岂友我耶”和苏东坡所谓“如必胜己而后友,则胜己者亦必不吾友矣”的悖论难题便潜伏其中,诸多缠绕牵强的解释,其实都是自觉不自觉地为此弥缝。然则,如此断句既然讲不通,可否另为断句?
窃以为,孔子的这段话应该这样断:
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这样断句,既在句法上说得过去,整段话也语义自足,而无须增字解经或牵强缠绕的解释。按,“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几句,原是《学而》篇一章里的一段,那一章的全文是:“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从全章上下文来看,“主忠信”的主语就是承前句而省的“君子”,“主”的古训是“亲”,其实“主”也有“以……为主”或“重视”、“看重”之意,则“【君子】主忠信”也即“君子看重忠信”;紧接着的“无友不如”之“如”是“及”的意思,“不如”犹“不及”、“不能”,而所“不及”或“不能”的宾语,就是前面已强调过的“忠信”,如此,则“无友不如”就是“不与不忠信的人交朋友”之意。这仍然是承前省的句法。并且,下句的“过”有了“己者”做主格,也责任分明——其实“己”做主格就够了,之所以加上语助词“者”凑成“己者过”乃是为了与“勿惮改”前后相称,这样一来“己者过则勿惮改”就前后语辞平衡、上下语义自明,无烦解释。把“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翻译为白话,大意如下:
【君子】最看重忠信,不与不忠信的人交朋友。自己有了过错,也不要怕改正。
要说孔子为什么会特别强调“【君子】主忠信,无友不如”也即“君子看重忠信,不与不忠信的人交朋友”?那是因为在孔子看来,“忠信”是朋友相待的底线——人是否与某人交朋友,最主要的就是看那个人是否“忠信”,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看那个人是不是信得过、靠得住。当然,朋友间的“忠信”是彼此相对待的,人不能片面要求朋友忠信而自己不忠信。本章“【君子】主忠信,无友不如”谈的是君子对朋友的忠信要求,而本篇前面一章是“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谈的则是君子对自己待朋友是否忠信的自我反省。前面还有一章记录子夏之言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此篇既有曾子、子夏关于待朋友是否够忠信之言,又有夫子的“【君子】主忠信,无友不如”之论——夫子之言正是曾子、子夏之所本。综合孔门师生的这些言论,正好说明“忠信”是朋友相对待之道,这就尽够了。至于是否“同志为友”、“见贤思齐”、“进德辅仁”等,都不是这里要谈的问题,前人拉扯这些东西,是因为“无友不如己者”的误断导致了解释的困难,因而不得不增字解经、强为之说。现在改正了这个误断,则一切都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了。
2、“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本义为何?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出自《为政》篇,是孔子对“诗三百”的总评。
“思无邪”原是《诗经》鲁颂《駉》诗的成句。《駉》诗四章,每章最后两句分别作“思无疆,思马斯臧”、“思无期,思马斯才”、“思无斁,思马斯作”和“思无邪,思马斯徂”。孔子此处当是借用《駉》诗成语,并且是“断章取义”的引用——“思”在《駉》里原是无意义的句首语助词,但孔子引来论诗时,“思”则变成了有意义的实词,由此,“思无邪”成了孔子对”诗三百”的总评,也是他的诗学总论。按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并不难解,历来的解说却几乎一致地将它道德化。盖自《毛诗序》强调“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以来,这种道德化的趋向就成为对“思无邪”的解释导向。现存最早的是东汉包咸的解释,包咸《论语包氏章句》已佚,但何晏《论语集解》的皇侃疏还保存了包咸对“思无邪”的解释:“包曰:归于正”(转引自1—165)。皇疏进一步联系《为政》篇的首章“为政以德”并引魏卫瓘的解释,从而对“思无邪”做出了这样的道德化疏解:“此章举《诗》证为政以德之事也。《诗》虽三百篇之多、六义之广,而唯用‘思无邪’之一言以当三百篇之理也。……言为政之道,唯思于无邪,无邪则归于正也。卫瓘云:‘不曰思正而曰思无邪,明正无所思邪,邪去,则合于正也’”(转引自1—166)。邢疏亦谓:“此章言为政之道在于去邪归正,故举诗要当一句以言之,……曰‘思无邪’者,此《诗》之一言,鲁颂《駉》篇文也。诗之为体,论劝颂德,止僻防邪,大抵皆归于正,故此一句可以当之也”(2—320)。从二程到朱子仍然沿着这个道德化的方向解释“思无邪”,但也开始对这个正统的解释有所反思。如朱子《论语集注》对“思无邪”的解释是:“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故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3—53-54)然后朱子又引程子之言曰:“‘思无邪’者,诚也。”(转引自3—54)有趣的是,朱子既是严于伦理的理学家,又是博学的语文学家,他显然意识到《诗经》的复杂性,诚所谓诗有正者有不正者,于是朱子转而强调它们对读者各有道德上的感发或惩创作用,而其结果都可以使读者归于正——“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这解释就不免迂回曲折了。程子则不愿细究而以简驭繁,断言“‘思无邪’者,诚也。”这一字解仍然坚守着理学家正心诚意的道德思路,而问题也从此埋下,迟早要爆发。
刘宝楠《论语正义》就修正朱子之论而认同孔子删诗之说,强调感发惩创原是作诗者之初心,“今直曰‘诗三百’,是论《诗》,非论读《诗》也。盖当巡狩采诗,兼陈美刺,而时俗之贞淫见焉。及其比音入乐,诵自瞽矇,而后王之法戒昭焉。故俗有淳漓,词有正变,而原夫作者之初,则发于感发惩创之心,故曰‘思无邪’也。”(4—40)近人郑浩《论语集解述要》则认为“思”无义,“邪”是“虚、徐”的意思,“无邪”即“无虚徐,则心无他骛”,于是对“思无邪”另提“别解”道:“夫子盖言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即所谓‘诗言志’者,此三百篇之所同也,故曰‘一言以蔽之。’惟诗人性情千古如照,故读者易收感发之效。若夫《诗》之是非得失,则在乎知人论世,而非此章论《诗》之本旨也。《集注》惟不考‘邪’为虚徐,又无奈其有淫诗何,遂不得不迂回其辞,为‘善者感发善心,恶者惩创逸志’之语。后人又以《集注》之迂回难通也,遂有淫诗本为孔子删弃,乃后人举以凑足三百之语。又有淫诗本非淫,乃诗人假托男女相约之语。因此字之不明,纠纷至今未已。”(转引自5—86-87)程树德《论语集释》进一步发挥郑浩之论:“窃谓此章‘蔽’字当……训‘断’。‘思’字乃发语辞,非心思之思,当从《项说》(指宋项安世《项氏家说》——引者按)。‘邪’字当作‘徐’解,《述要》之说良确。合此三者,本章之义始无余蕴。”(5—87)郑浩和程树德把“思无邪”解为“无虚徐”,以此证明诗出于作者的真性情,诚然用心良好,却不免减字改字解经之嫌。
杨树达的《论语疏证》对“思无邪”仍然坚守着“观风俗、正得失”的正统兼笼统的解释,文长不录。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对“思无邪”没有强为之说,只简明地注释说:“‘思无邪’一语本是《诗经》鲁颂《駉》篇之文,孔子借它来评论所有诗篇。思字在《駉》篇本是无义的语首词,孔子引用它却当思想解,自是断章取义。俞樾《曲园杂纂·说项》说这也是语辞,恐不合孔子原意。”(7—11)这个注释虽无新意,却祛除了此前的一些牵强曲折的解释,提醒读者体会孔子的原意。杨伯峻对此章的翻译,也把过于严苛的道德纯正改为“思想纯正”——“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7—11)钱穆的《论语新解》先引用了诗思归正的传统说法,接着又引另一说——“又一说,无邪,直义。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露,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假,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钱穆认为“后说为优”,并补充说“‘思’乃语辞,不作思维解”(8—17)。看得出来,钱穆所采纳的其实是程子到郑浩的看法。
这就是“思无邪”的解释史之大概。盖自汉代确立以儒家礼教为治国之大本,对《诗经》的解释就趋向于以礼解诗,《毛诗序》即是典型。连带地也影响到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解释,孔子的话其实并无明显的道德色彩,却由于“以礼解诗”的风气,于是“思无邪”被理解为“论劝颂德,止僻防邪,大抵皆归于正”,就成为主导性的解释方向。朱子意识到《诗经》三百篇并非都“归于正”,实际上还有不少“淫诗”存于其中,所以他不得不曲折地从一切诗都有助于提高读者的道德觉悟来立论,以为“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刘宝楠、郑浩和和程树德等看到朱子解释的勉强,又有所修正。郑浩、程树德发挥程子“‘思无邪’者诚也”之论,以为“夫子盖言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即所谓‘诗言志’者,此三百篇之所同也,故曰‘一言以蔽之’”。应该说,从程子到郑浩、程树德构成了另一个解释方向。当代学者李泽厚也采此说,以为“‘思’是语气助词,不作‘思想’解,‘邪’也不作‘邪恶’解。”李泽厚赞同郑浩的解释:“盖言于《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所以李泽厚将此句译为:“《诗经》三百首,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不虚假。”[4]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新文化人也沿着这两个方向有进一步的发挥。鲁迅和罗庸可为代表。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对“思无邪”以及“诗言志”的批判是很著名的:
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虽然,上极天帝,下至舆台,则不能不因此变其前时之生活;协力而夭阏之,思永保其故态,殆亦人情已。故态水存,是曰古国。惟诗究不可灭尽,则又设范以囚之。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5]
鲁迅站在新的人学和诗学立场上尖锐批判了“思无邪”的古典诗学,可他对“思无邪”的理解却仍然沿袭了性情之正的传统论调,并未反思这种正统解释是否符合孔子之本意。
罗庸出身于北大哲学门而后成为古典文学研究者,曾任西南联大国文系主任。罗庸对《论语》有一个从随意玩习到体验力行的过程,逐渐对儒学有同情的体认,抗战时期撰写了多篇关于儒学和孔子的文字,结集为《鸭池十讲》,其中的一篇就是《思无邪》。此文开首便道:
说起《沦语·为政》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一章,觉得不容易用浅喻一语道破。古今善说此章者无如程子,那是再简要没有了;却被朱子引作旁参,《集注》里还是说使人得性情之正一类的话。清代汉学家说鲁颂,更多新解,但和《论语》此章大义全无关涉;也许鲁颂的“思无邪”另有本义,但至少孔子引用时已非旧义了。《集注》立意要圆成美刺法戒之说,却无意中已落到道着用便不是的地步。我以为最好还是程子的话:“思无邪者,诚也。”这真是一语破的之论。
然后,罗庸便指出朱子在《朱子语类》中关于“思无邪”的十几条问答中颇不一致的支绌之解,盖因朱子意识到《诗经》中确有“淫奔之诗”,他觉得这些诗有背于夫子“思无邪”之断言,于是不得不曲为解说、增字解经,以保全“诗无邪”乃“归于正”之正论。这在朱子实非得已。罗庸有破有立道:
说古书只要少存些《春秋》为汉制法的意思,葛藤便会剪除不少;况且《论语》本文只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并未说“其义使读者归于无邪。”则美刺法戒之说于何安立?
所以“思无邪”最好就是“思无邪”,不须旁征博引,更不须增字解经,若必须下一转语的话,那末,“思无邪者,诚也。”
如前所述,“思无邪者,诚也”正是程子的解释。罗庸肯认程子此解确是一语破的之论。只是有感于程子的解释太过简要,所以罗庸给出了一个更为详赡也较为现代的讲解:
我们读一篇好的作品,常常拍案叫绝,说是“如获我心”,或“如我心中之所欲言”,那便是作者与读者间心灵合一的现象,正如几何学上两点同在一个位置等于一点一般。扩而充之,凡旷怀无营而于当境有所契合,便达到一种物我相忘的境界,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便是文学内在的最高之境,此即“诚”也。诚则能动,所以文境愈高,感人愈深。
“思无邪”便是达此之途,那是一种因感求通而纯直无枉的境界。正如几何学上的直线,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一般。凡相感则必求通,此即“思”也,“无邪”就是不绕湾子。思之思之,便会立刻消灭那距离而成为一点。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说:“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思得仁至,必须两点之间没有障碍不绕湾子才行。
……
所以文字的标准只须问真不真,不必问善不善,以真无有不善故。天下事唯伪与曲为最丑,此外,只要是中诚之所发抒,都非邪思,一句“修辞立其诚”,而善美具矣。
性情的界域到直线为止,文学内容的界域也到直线为止,一入于面便是推理的境界,举一反三,告往知来,便都是推理之境,非复性情所涵摄了。
理智到成了立体便是过胜,俗语说“八面玲珑”,即言其人之巧黠。成了球体便是小人之尤,元次山之所以“恶圆”,恶其滑也。
故文学内在之境以点为极则,文学外形之标准却要成球体,看似相反而实相成。盖文笔不能如珠走盘只是无力,而无力之故由于内境之不诚,倘使一片真诚,未有不达者,达则如珠走盘矣。
所以“思无邪”不只就内容说,外形之能达实亦包括在内,此所以“一言以蔽之”也。[6]
应该说,罗庸的解说较近情理,只是他忽视了其所采纳的程伊川之解仍带有“正心诚意”的道德论痕迹。并且,罗庸把“思无邪”解释成情思与艺术必须同样纯直无枉,这也有点贪求其全了。其实,真纯的情思既可以率直表达,也可以曲折表达,固执其一就欠通达了。
我对历来关于“思无邪”的解释之怀疑,就始于《摩罗诗力说》的严厉批判。鲁迅是以历来道德化的解释无误为前提来展开批判的,这反而启我疑窦:夫子说“思无邪”当真如鲁迅所批判的那么坏心眼、那么罪孽深重吗?回想初读“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直感,怎么想也是好话啊!此后仍然感到,孔子此言虽简而语义自足,并不坏也并不难懂,可是翻看历来的解释却那么复杂曲折,其主导性的解读则把它解成礼教气—道学气十足的道德判断,难怪鲁迅要严厉批判了。至于从程伊川到郑浩、程树德、罗庸和李泽厚的“别解”,诚然较近情理,但仍然暗含着一丝礼学-道学气味或某种认识真伪论之色调,故为我所不取。
直到今天,我对夫子此言的理解仍一如四十多年前初读时之直感。的确,“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委实是孔子对“诗三百”的由衷赞叹,赞叹全部“诗三百”的诗思很无邪,简洁明了、清通自足,近于大白话,根本不必添字解经或改字解经,略加疏通,读者即可理解。所以翻译此言成白话,近乎多此一举,但还是按惯例翻译一下:
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情思真无邪啊!
下面说说我的理解:《诗经》鲁颂《駉》篇里的“思无邪”之“思”的确是无意义的发语辞,但在孔子引用此言的语境里,“思无邪”之“思”肯定是有意义的实词,“思”就是诗三百所表现的“诗思”。这些“诗思”不会是杨伯峻先生翻译的“思想”,因为诗确如罗庸所说不是思想的推理和说明,而是诗人的情感和想象之表现,为免繁琐,这里就简单译为“情思”——“情思”乃是情感和想象的简缩。应该承认,孔子是一个真爱诗也真懂诗的人,他不会用道德之纯正或思想之纯真来要求“诗”的。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的解释和翻译也不取程伊川以来的“诚”字之解直至李泽厚的“不虚假”之说,而是直如“思无邪”字面之所言,乃是夫子阅读“诗三百”后的美感之欣然流露。虽然确如郑浩所言:“夫子盖言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但“诗三百”却并非如郑浩接着所说的是“毫无伪托虚徐之意”,恰恰相反,“诗三百”除了个别篇什如许穆夫人所作《载驰》外,大多数诗篇所写情思都出自诗人的拟想、想象、假托,懂诗的孔子当然认识到这一点。就此而言,“思无邪”正是一个无关情思真伪的审美判断。并且,“诗三百”既有雅与颂之诗,也有不大雅的诗如郑风、卫风里的爱情诗,这些爱情诗后来被朱子称为“淫诗”,但并无根据说当年的孔子也这么道学地看待它们,其实孔子也同样欣赏爱情诗,同样觉得它们是“思无邪”的。即使撇开郑卫之诗不论,《周南》、《召南》确知是孔子很欣赏的,《阳货》篇特地记载了孔子对儿子的提醒:“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而《周南》、《召南》之诗多言男女之情,《周南》的首篇就是婉转缠绵的爱情诗《关雎》,孔子很欣赏这首“思无邪”的好诗,并赞叹“《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的音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必须明辨的是,孔子所谓“淫”并非“淫荡”之“淫”,而是“乐感过分”的意思,“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表现的乃是孔子对音乐的趣味,与诗意无关——孔子并未像汉儒那样把《关雎》曲解为“美后妃之德”、“正夫妇之道”的道德诗。尽管司马迁说过:“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7]从此有了孔子曾按礼义删编《诗经》之论,但这只是司马迁的推测之词,并无什么根据。究其实,孔子是一个“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人,他当日看到的并拿来教学的”诗三百”已有成编,其篇目与后来“三百五篇”(加上有目无文的“笙诗”六篇,则共计三百一十一篇)的《诗经》并无不同,并且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的,乃是“诗三百”的音乐而非文辞。所以诚如朱子所揭示的,孔子倘据礼义删诗,则《诗经》就不应有那么多“淫诗”啊!这也反过来证明,孔子当日并没有用什么邪正的道德观念看“诗三百”,他的“思无邪”之说乃是对所有“诗三百”而发的赞叹——欣然赞叹全部的“诗三百”都是纯粹的生活经验及基于这些经验的情感与想象的率性表现——则其叹赏之言“思无邪”岂不正是今日所谓基于阅读-审美经验而来的审美判断吗?!我们应该承认,从《论语》及相关历史文献来看,孔子其实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他对男女之情并无严苛不近人情的要求,他生活的时代也没有那样的要求,事实上,那时的社会习俗和婚姻制度倒是每逢“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8]就连孔子本身也是其父母自由“相奔”的爱之结晶啊!由此可见,历来所谓孔子严守男女之大防的刻板形象乃是后儒强给他的,早该给夫子平反了!
本文原文分上中下三篇,连载于《名作欣赏》2020年第4期、第5期、第6期,经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解志熙教授授权发布。
注释:
[1]《四书或问》第1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2]南怀瑾:《论语别裁》第32-3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
[3]李泽厚:《论语今读》第26-27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
[4]李泽厚:(《论语今读》第35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
[5]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6]以上引文均见罗庸:《思无邪》,《国文月刊》第1卷第6期,1941年2月出刊。按,此文收入《鸭池十讲》,开明书店,1943年初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新版。
[7]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引文据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1160-11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8]《周礼·地官·媒氏》,《十三经注疏》第733页,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