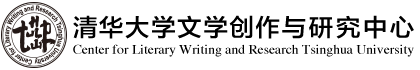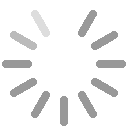清华文学研究 | 西渡:散文诗的性质与可能
2020.07.06
“清华文学研究”栏目旨在推介清华学人在文学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促进学术交流。
散文诗是一个相当含混的概念。我们用这个名称来称呼从完全的诗到完全的散文甚至是拙劣的散文的许多大不相同的东西。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圣琼·佩斯的《阿纳巴斯》,屠格涅夫的《爱之路》,泰戈尔的《吉檀迦利》,纪伯伦的《先知》,鲁迅的《野草》,统统被称为散文诗。要从这些相去悬殊的作品里,给散文诗的性质做一个总结是困难的。散文诗到底是什么?瓦莱里认为,人们对语言的使用存在两极,一极是音乐(也就是他说的纯诗),另一极是数学。在这两极之间,是诗和散文的各种过渡状态。散文诗无疑属于典型的过渡状态的概念。但是,这样的解释几乎无助于我们对散文诗的理解,我们对这一文体的种种疑惑也无从解除。散文诗在诗和散文的过渡地带中,偏向于诗的一端还是散文的一端?或者说,散文诗是诗对散文的占领,还是散文向诗的侵入?它是诗的内容而采用了散文的形式,还是散文的内容而加以诗的装饰?这些都是疑问。
也许有人认为,这些都是无谓的问题。散文诗就是散文和诗的混合,知道它有几分像诗,又有几分像散文就行了。实际上,这种模糊的认识对创作和批评不但是欠缺的,而且是有害的。叶维廉就曾批评“不少中国作家,尤其是大陆的作家,只把散文略加美化便冠之以散文诗之名,其实,它们往往只是一种美化的散文而已,没有诗的‘触动’”。[1]如果作者在下笔之先对散文诗的性质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他笔下的作品势必变成非驴非马的东西;如果批评家对散文诗没有一个恒定的,起码是相对稳定的尺度,那么他对于作品的判断也必陷入游移不定之中。
诗和散文是两个性质非常不同的东西,这两个东西并不是在什么情形下都能进行嫁接。诗和散文属于两种想象世界的方式。小说把世界想象为一个故事,戏剧把世界想象为一场冲突,连普通的读者也熟悉这样的分别。但对于诗和散文的分别,即使是专门的研究者也很少知其所以然。在我国自古就有深厚的诗意散文传统的文化氛围中,更容易忽略这种差别——我们很容易把散文和诗的分别仅仅停留在纯形式的层面,即有无规律的音节和是否分行上。实际上,诗和散文的分别首先体现在两者不同的思维方式上。诗以感性、直觉的方式感受、领悟世界,散文则以知性的方式观察、思考和认识世界。
诗献身于未来,如果用更加散文的语言来表述,可以说诗具有未来性。诗所面对的世界是未成的,散文所面对的世界是既成的;诗的世界是可能的,散文的世界是实存的。也可以说,诗歌创造世界,散文解释世界。奥登说:“追随着雅典的泰门,柏拉图说过,音乐模式改变之后,城墙会受到震动。也许,更为正确的说法是,模式的改变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城墙将会震动。然后,艺术家最早体验到了政治行动中爆发的社会变动,他们感觉到当前的表达模式不再能够处理他们真实的关切。”[2]兰波说,诗人是通灵者,庞德说,诗是一个种族的触须,诗人们都自信于能够从未来接受信息,把未来的消息告知人们。散文服务于现实,处理各种现实的事务是它的本分,这样的任务和职司使它根本没有余裕接受未来的信息,即使诗人写的散文也是如此。
诗具有一种完全性。诗的思维方式是直觉的、隐喻的、象征的,它是对世界的本质和整体的领悟。在诗中,有限的诗的形象总是暗示着无限的、作为整体的世界。极而言之,一首诗自成一个宇宙。因此,诗拒绝依附任何现成的力量,它在铁板一块砖中看出缝隙,在看似遥远的两岸搭起桥梁。散文的思维则是逻辑的、推理的。散文总是试图把自己证明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它也就甘愿停留于有限和局部。按照语言学家洪堡特的意见,诗和散文都从现实出发,但诗“从感性现象的角度把握现实”,“但它非但不关心现实的本质特性,反而故意无视这种特性”,“于是,诗歌通过想象力把感性的现象联系起来,并使之成为一个艺术-观念整体的直观形象”;而“散文则恰恰要在现实中寻找实际存在的源流,以及现实与实际存在的联系。因此,散文通过智力活动的途径把事实与事实、概念与概念联系起来,力图用一种统一的思想体现出它们之间的客观关系。”[3]诗所创造的世界,不能说与我们身外的世界无关,因为我们对外在世界的经验显然是诗的创造的动力和材料来源的重要方面,但作为完成的作品,诗的世界并不依赖于外在世界,而是平行于、独立于外在世界。它作为诗的价值也在于此。诗越独立、越自足,它的价值就越完全。换句话说,诗正是通过它的独立与世界发生联系。这种文本对于现实的自足是诗的完全性的一个方面。诗的完全性的另一方面体现在诗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废名说:“一首新诗要同一个新皮球一样,要处处离球心是半径,处处都可以碰得起来。” [4]这个球心就是诗的内容,皮球的表面就是诗的形式,诗的形式处处都要符合内容的要求,处处离球心是半径,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不允许稍有松懈,所以它要是充满了气的新皮球。换一个足球的比喻,足球场上只能有一个球,如果球场上有两个球,比赛就无法进行了。在球场上,双方队员都围绕球而行动,即使离球最远的队员,其移位也是围绕球的。只要稍微懂得足球比赛的规则,就能看出这一点。但假若有一个来自外星的智慧生物,完全不懂球赛的规则,他大概会感到球场上的移动毫无规律。而假若有一个韩复渠,他就要给场上的每个人发一个球了。总而言之,诗的自为要求它有一个有力的、内在于自身的核心——这就是诗的政治。散文既不是这样自为的存在,内容和形式之间也就不存在这种唯一的关系。散文的价值和意义取决于它和外在世界的关系,譬如它对世界的观察是否准确,它对世界的解释是否正确、能否得到客观的验证,以及能不能依赖这种解释去干预世界,得到某种实际的效果。也就是说,散文以实用为目的,而且正是其实用价值的大小决定了散文价值的大小。散文因而总是依附于传统、习俗和伦理。散文的形式是可以被替换的。只要能够达到其设定的应用目标,它的形式可以有无数的替身,可以抻长,可以截短,可以催肥,也可以减肥。在散文中,形式本身是一个累赘的、多余的存在,一旦散文的形式获得了某种独立的意义,散文也就获得了某种诗的性质。这就是我们说某些小说、剧本、散文具有诗性的原因。这个意义上的诗是一种广泛的存在,当然它是一种不完全的诗,是诗向散文的渗透。也可以说,是散文向诗偷来的东西。无疑,这种诗性提升了散文的品质。但如果这种偷来的东西变得过分,以至有碍于散文实现自己的实用目的,也会把散文压垮,成为非驴非马的东西,譬如种种华而不实的应试文章、官样文章。

废名
诗的未来性和完全性的叠加,体现为诗的超越性。未来性是时间的超越,完全性是空间的超越。这两种超越在散文里都无法实现。散文依附于当下的时间,也依附于过去的时间——它从过去和传统借来力量,服务于当下的有限的目的。散文的空间是有限的,诗的空间是无限的。诗以它的自足和完全实现了对有限空间的超越。所谓语言的诗性指的就是语言的这种超越性。有人写了一辈子诗,却从未达到这样的超越,甚至从未意识到超越在诗中的存在,他只是写了一辈子散文而不自知,即使他一直写的是分行的、押韵的乃至格律的辞章。艾略特在《什么是次要诗歌》中提到我们对某些被冠以诗歌之名的文本的一种可能评价:“如果这是诗歌,它将是重要的——但它不是。”[5]在当下诗坛,这种鱼目混珠的“诗”大量存在,以至于淹没了真正的诗。如何鉴别这些诗的赝品?是否具有这种超越的性质,我相信就是最好的试金石。
那么,诗真就毫无实用目的了吗?诗对现实真就毫无作用了吗?诗不能阻挡坦克,但诗可以改变坦克手。诗通过改变人心而改变现实。也就是说,诗有改变现实的潜能,它是一种长期的、隐含的力量,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诗也能发挥即时的作用。然而,无论如何,诗对现实的影响只是一种偶然的、暂时的作用,它本身并不以影响、改变现实为目的。也就是说,超越性始终是诗的最高的、终极的目标,在这目标之下,它当然也不拒绝对现实发挥一点余热。说到底,如果诗也有什么实用目的的话,那就是通过保卫语言而保卫人之存在。我们总认为,语言是为实用目的而发明的,诗的功能是对语言的一种特殊用法,而这种用法是违背了语言的一般目的的。但是,按照法国哲学家杜夫海纳的看法,语言可能首先是作为诗发明出来的,它所显示的是“自然的诗歌潜能”。他说:“言语是从自然中涌现出来的”,是“事物为自己命名”。这种自我命名的行为也就是诗。维特根斯坦也有类似的看法:“当言语在欢乐时,它就诞生了。于是,我们可以放心地想象:命名就是灵魂的某种独特的行为,是灵魂给一个物体取名字的方式”。“言语在欢乐”,对于诗歌中的语言的性状,实在没有比这更精确的描绘了。杜夫海纳进而指出,“当人们把艺术看作语言时,总是想方设法通过语言去理解艺术。也许应该进行相反的动作,即通过艺术去理解语言。” [6]诗和语言在其源头实在是二而一的。但是,人类的实用的目的改造了语言,把语言变成了自己的手段,语言的诗的功能因而日渐削弱,它的实用功能却越来越根深蒂固,竟至于人们忘记了它的诗的出身。这个时候就该轮到诗人出场了。诗人何为?说到这个问题,80年代的诗人们都喜欢引用海德格尔引用的荷尔德林来回答这个问题:“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 /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实际上,诗人 就是献身于语言的诗歌职责的那种罕见的人,换言之,就是为语言的欢乐而工作的人。所谓“酒神的神圣祭祀”,其职责就是如此。语言在被欢乐点燃之前,没有光,没有声音,和大地上的万物一起沉睡着。而诗人就是那个在神圣的黑夜中唤醒语言,重新发明语言的人。在应用的劳碌中沉睡的语言,于是被诗人重新创造、发明出来。而这个创造、发明的过程必须不断地进行。因为,实用性就像是语言的家族诅咒,一旦发明的过程终止,语言就会因这诅咒陷入昏睡,就像那个童话中的睡美人一样。语言的诗性仰赖于诗人持续的发明,诗则通过不断发明语言而发明自己——这实际上是一回事。否则,语言会因失血、腐败而死亡,诗也会因为语言的死亡无处存身。
上述这些可以说是诗和散文在性质上的最大分别。
诗和散文形式上的分别是最容易观察到的。形式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节奏和韵律的有无的问题。诗以感性的、情感的方式领受世界,不同的情感对应着不同的生理条件和反应,而各有其特定的呼吸和节律。这种情感加上语言推进的时间因素,便成为诗歌的节奏。也就是说,诗歌中的情感总是音乐化了的。其音乐化的程度,也就是诗的纯粹的程度的指标。所以,瓦莱里认为纯诗是完全的音乐。诗的推进所依赖的主要就是这个音乐的力量。显然,诗的节奏和韵律并不独立于诗的内容,它和诗的内容实际上是一个东西。而散文的推进则主要依靠逻辑的力量。散文毋须借助音乐的力量,而且音乐有可能对散文的内容造成损害。我们很难想象一种音乐化的数学。事实上,音乐化不但不能增强散文所依赖的逻辑力量,而且会降低这个逻辑的力量。我们有时以数学比拟诗的简洁和精确,但这并不意味着诗和数学在性质上有什么相同之处。
既然诗和散文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这样的分别,那么诗和散文的结合,在何种方式、什么程度上是可能的呢?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诗和散文的结合是不可能的。早在波德莱尔发表他的系列散文诗之前,洪堡特就对诗歌和散文的混合发表过中肯的意见:“只就其形式的一方面来看,内在的散文倾向应当会发展成为带格律的言语,而内在的诗歌倾向也可以发展成为自由的言语。然而,诗歌和散文多半都会因此受损,其结果是,以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散文内容既不完全具备散文的性质,也不完全具备诗歌的性质。以散文形式出现的诗歌,也同样如此。”[7]洪堡特的意思是,如果只就形式来看诗歌和散文的问题,那么散文的内在目标尽可以在格律的语言中得以实现;而诗歌的内在目标也可以在自由的语言中实现。但洪堡特认为,诗歌和散文的形式最终都受制于它们所要表现的内容,从而约束了它们各自的反向运动。也就是说,诗所以有诗的形式是因为它有诗的内容,散文所以有散文的形式也因为它有散文的内容。诗的内容就应当用诗的形式来表达;只有这样,诗才能达到自身的完全,散文也才能达成其本身的应用目标。然而,终身执着于纯诗的瓦莱里也说了,纯诗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因为诗所使用的工具就是不纯的,或者说语言本身就是散文的。——这种语言的实存状态,可以说是杜夫海纳“从自然中涌现的语言”的堕落情形。也就是说,纯粹的诗只是一个理想的远景,而实存的诗总是诗和散文的某种结合。那么,诗的内容和散文形式某种程度的结合,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这个意义上的散文诗是脱去了诗歌袍服的诗,也就是郭沫若所谓的裸体美人。波德莱尔的散文诗《失落的光环》也许可以认为是对散文诗的文类性质的某种揭示。这首诗写一个诗人在死亡横行的泥污的马路中间丢失了诗的光环。紧接着波德莱尔说了下面的话:“我告诉自己,任何坏事都有它好的一面……现在我可以微服出游,不带任何阶级的行为意识,可以纵情享乐,像常人一样。”这篇作品一方面揭示了在工具理性(它在诗里以死亡的面目出现)横行的世界上,诗的灵性的光芒是如何失去的,另一方面也暗示诗在失去了诗的光环之后——我们不妨将此理解为诗从诗的形式中的解放——却获得了出入日常生活的自由,以及与常人打交道的能力。按照波德莱尔的这个意见,散文诗是伪装成散文的诗,其目的是以散文的、表面的理性逻辑,引领“散文”的读者于不知不觉中进入诗的领域。这点从波德莱尔散文诗的创作实践也可看出大概。波德莱尔常常是先写了诗,然后把诗再改写成散文。散文诗必以真正的诗情为出发点,这点在波德莱尔那里是很清楚的。
那么,散文的内容和诗的形式是否也能结合为散文诗的一种类型呢?理论上似乎不能否定这种可能。表面上看起来,这样的结合比诗的内容和散文形式的结合要更容易,因为散文的内容总比诗的内容来源丰富,而形式的模仿似乎总是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来达到的。但实际上,这种结合的效果是很可疑的。诗的内容出之以散文的形式,结果是内容大于形式,其失在朴;言而无文,仍可谓言之有物。散文的内容加上诗的形式,结果是形式大于内容,其失在华;巧言令色,不但使诗的形式变成了散文的附加装饰,而且存在文学伦理上的瑕疵。这样的散文诗极易演变成一种矫揉造作的文体。可以说,散文的内容用诗的形式来装饰往往是得不偿失的。
从散文诗的起源来看,也是以诗的内容而出以散文的表达形式者为正宗。散文诗的鼻祖波德莱尔给散文诗所作的界定“心灵的抒情的冲动、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跳动”[8],可以说完全属于诗的内容——它们是对可能世界的领悟,而不是对实存世界的解释。波德莱尔告诫自己,“永远做一个诗人,即使在散文中”。[9]散文诗是伴随着欧洲现代诗运动而诞生的。现代诗最典型地表现了觉醒的或者说是迷惘的诗人对西方世界具有悠久传统而在工业革命之后达于顶峰的工具理性的反叛,具体来说就是以建基于本能之上的直觉、情感和想象反抗拜物的、反灵性的工具理性—资本现实。在波德莱尔笔下,散文诗正是反抗工业时代物质主义现实的利器。为什么诗要伪装成散文?波德莱尔的《失去的光环》给出了一部分的理由——为那些已经被工具理性—物质主义现实损害了心灵完整、失去了诗歌感悟力的现代人搭起一座进入诗歌的桥梁。叶维廉先生论述散文诗的文论标题,《散文诗——为“单面人”而设的诗的引桥》,即揭出了散文诗的这一性质,可谓富有卓见。此外,对诗歌的古典形式的反叛也是波德莱尔等现代诗人采用散文诗形式的重要考虑。诗歌严谨刻板的古典形式,同样是西方唯理传统的产物,是其唯理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一环。这一形式是等级的、专制的,它限制了诗歌感性的发扬,压抑了人的灵性。所以,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不仅是一场内容的革命,也是一场形式的革命。从内容上说,现代诗是以主体的直觉和感性反对客体主义的工具理性,从形式来说则是以形式的松动、松绑和解放来反对严格而近于专制的古典形式。散文诗就是伴随着这一形式解放运动,和自由诗一同产生的。所以,从文学史角度而言,散文诗一直是现代诗的一个门类,而不是现代散文的一个门类。正因为如此,散文诗的优秀作者多为杰出的诗人,而屠格涅夫这样的小说家所写的所谓散文诗就算不上散文诗的当行本色。

波德莱尔
散文诗的文体缺陷因此也是明显的。散文诗必须依附于诗,或者依附于哲学。只有两种人能够写散文诗:一种是真正的诗人,另一种是真正的思想者。也就是说,散文诗不能依靠自体繁殖,它必须从其他文体获得它的遗传密码。这就像驴和马的结合所生的骡子,它兼有驴和马的若干优点,但它最大的缺陷就是不能繁殖后代。
由上述考察,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散文诗从性质规定上说是诗的,而不是散文的;它是诗的内容和散文形式的结合,而不是散文的内容和诗的形式的结合。散文诗和诗一样都必须有诗的内容。散文的内容很难装扮成诗,诗的内容却可以伪装成散文。诗和散文诗的区别不在内容,而在形式。散文诗随其形式与诗接近的程度而趋向于诗或散文。其形式愈近于诗,则其文类归属愈趋向于诗;其形式愈近于散文,则其文类性质也愈趋向于散文。诗伪装成散文,当然要在诗情上付出代价。弗罗斯特说,诗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而诗译成散文的损失也许要大于诗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损失。这是由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诗的思维方式的根本差异造成的。但散文诗也拥有自己的优势——它以散文的伪装解除了“单面”的现代人(也就是“散文”的人)对诗歌的抵制,并成功地把他们诱入诗歌的领域——这也许就是散文诗的文体价值。
然而,是否存在另外一种散文诗的可能呢?它既不是散文伪装的诗,也不是诗伪装的散文,而就是地道的、如假包换的散文诗?废名在1930年代竭力主张新诗是自由诗,到了1940年代,由于卞之琳、冯至等人在新诗格律探索方面的成功尝试,废名认识到新诗的自由还有更大的空间,这个空间甚至大到可以把格律也包括在内。废名说,十四行体在冯至手上“真是有助于诗情了”“冯至的诗确是因十四行体而好了”。就此,废名做一个精当的说明,“十四行体也不过是分行之一体罢了”,它“是你自己的自由,并不是新诗的形式”。[10]废名的意思是,存在一种特殊的诗情、特殊的诗的内容,按照形式和内容一致的要求,它恰恰适合用十四行体来表达,那么这个十四行就不是格律,而是新诗的自由原则的体现。同理,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某些特殊的感兴、情调,它恰恰适合且只适合用散文诗这样一种形式来表达。对于这样的情形,我们可以循废名的先例说,散文诗也是诗的自由的一种。这样的散文诗不同于波德莱尔由诗改写的散文诗,更不同于用诗装饰的散文。也许,这样的散文诗才是散文诗这个特殊文体的正宗,应该成为所有散文诗作者追求的目标。
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曾将散文诗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寓言,注重情节;第二类以兰波的《彩画集》为典范,注重意象;第三类是勃莱本人提倡的客体诗,注重客体。勃莱的这个区分着眼于散文诗内部的关系,并无助于我们认识散文诗的性质。我认为为着这个目标,我们先有必要对那些被笼统称为散文诗的东西进行文类的区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对它们与诗的关系进行一番考察。在我看来,圣琼·佩斯的《阿纳巴斯》完全是诗,因为它虽然不分行,却仍然具有极为生动的、一点不亚于分行诗的节奏与韵律,完全体现了诗歌的“音乐的精神”。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虽有诗情,形式上却已近于散文,它和贝尔特朗《夜之卡斯帕尔》开创了散文诗的时代,却难称散文诗的正宗。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基本上属于诗,它有散文的成分,但诗的节奏与韵律还很少受到散文成分的侵袭。纪伯伦的《先知》具有诗的内核,在形式上偏于散文,但仍保留了韵律的成分。《吉檀迦利》和《先知》庶几接近我所说的地道的、正宗的散文诗。与之性质相近的,还有果尔蒙的《西蒙娜集》,保尔·福尔的《法兰西巴拉德》,纪德的《地粮》。所以谓之正宗,就在于它们的内容和形式都具有严格的一致性,非这样的形式不能表达这样的内容,非这样的内容不得采用这样的形式。屠格涅夫的《爱之路》基本上是散文,因为它的大部分篇目不具备诗的内容,只有少数作品含有一定的诗的成分;它被称为散文诗,主要是因为它吸收了诗的一些形式因素。也就是说,它是试图装扮成诗的散文。鲁迅的《野草》则是一本混合的作品集,它的部分作品具有浓郁的诗情,如《影的告别》《死火》《复仇》(一、二)《希望》《好的故事》《失掉的好地狱》《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形式上也保留了诗的部分特征,这些作品可以称为出色的散文诗。《求乞者》《狗的驳诘》《颓败线的颤动》题材上近于屠格涅夫,思想则比屠氏深沉。《秋夜》《雪》《过客》《腊叶》有诗情,可惜表现太近于散文。它的另一些作品,则是完全的散文,如《风筝》《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立论》《死后》《一觉》。这些作品是对实存世界的某些局部的观察和解释,不是对全体的感受和领悟,因而没有上升为整体的、世界性的图像。
本文原刊于《诗刊》(上半月刊)2020年3月号,经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陈国平教授授权发布。图片来自网络。
注释:
[1] 叶维廉《散文诗——为“单面人”而设的诗的引桥》,《叶维廉文集》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页。
[2] 奥登《美国诗歌》,奥登《染匠之手》,胡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95页。
[3]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27-228页。
[4] 废名《十年诗抄》,废名《论新诗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5] 艾略特《什么是次要诗歌》,程一身译,《文学界》2011年第11期。
[6] 杜夫海纳《艺术与话语》,《西方现代诗论》,刘福春、杨匡汉编,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668页。
[7]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28页。
[8] 波德莱尔《献给阿尔塞纳·乌塞》(《巴黎的忧郁》序言),译文引自《恶之花·巴黎的忧郁》(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8页。“意识的跳跃”,叶维廉译为“意识之惊悸”,亚丁译为“良心的惊厥”,更能显示散文诗中的意识活动的“诗的性质”。
[9] 波德莱尔《诗艺》,《巴黎的忧郁》,胡品清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68页。
[10] 废名《<十四行集>》,废名《论新诗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