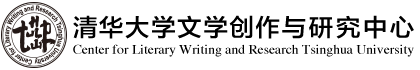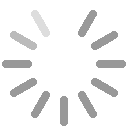清华文学研究 | 解志熙:《论语》疑难句解读(下)
2021.10.19
“清华文学研究”栏目旨在推介清华学人在文学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促进学术交流。
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究竟是什么意思?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出自《泰伯》篇。这是《论语》中最著名的一个问题句。
汉代对此句的训读就埋下问题,牵强的解释也便随之而生。近代以来,孔子此言引起不少争议,而迄今仍无定论。其实,问题并不难解决,下面就先述前人训断,再说说个人意见。
汉魏旧注当然没有标点,但从何晏《论语集解》对此句之注——“‘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也”(转引自1—215)里可以推知,汉魏人对此句的点读正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后的点读长期一仍其旧。何晏之注是从民的知能不及上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皇侃的疏解是:“此明天道深远,非人道所可知也。‘由’,用也。元亨日新之道,百姓日用而生,故云‘可使由之’也。但虽日用而不知其所以,故云‘不可使知之’也。张凭曰:‘为政以德,则各得其性。天下日用而不知,故曰:可使由之。若为政以刑,则防民之为奸,民知有防,而为奸弥巧,故曰:不可使知之。’言为政当以德,民由之而已,不可用刑,民知其术也。”(1—215)看得出来,皇疏及其所引东晋张凭的解读(张凭有《论语张氏注》),已显现出为政者担心民有知有防而为奸弥巧、故而不可使知之的政治蒙昧主义色彩。邢疏则将“元亨日新”的深远天道理解为圣人的深远之道,以为民的知力不能理解深远的圣人之道,所以邢疏这样解释孔子此言:“此章言圣人之道深远,人不易知也。‘由’,用也,民可使用之而不可使知之者,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故也。”(2—374)显然,邢昺又退回到民不能知的能力论上了。朱子的《论语集注》对此句的解释则非常简洁:“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3—105)这给人不愿多说、故意简化之感,其实朱子是担心深究此句,会把孔子与愚民主义挂上钩。按,《朱子语类》卷三十五记载:“或曰:王介甫以为‘不可使知’, 尽圣人愚民之意。”[9]可见朱子确实有所担心,所以他在《论语集注》注释后,紧接著就引了程子之言为孔子撇清了愚民主义的关系——“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耳。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3—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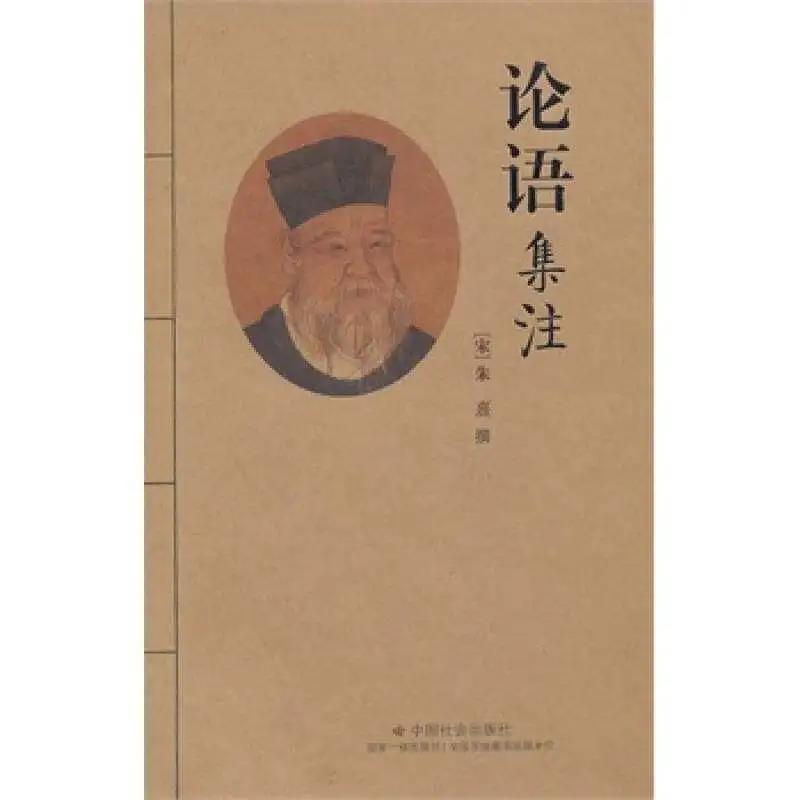
可是,程、朱的解释并未解决问题,“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矛盾仍是困扰人的问题,元明清的学者多在“民愚不可能知”或“愚民不可使知”之间拉锯,议论纷纭,难解难分,兹不具引。莫衷一是之际,也有人出来曲折解说、试图调停矛盾。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可为代表。刘宝楠对这两句的“正义”写得迂曲冗长,煞费折中调停之苦心。刘宝楠受凌鸣喈的启发,把“民可”一章与《泰伯》篇的上一章“子曰:兴於诗,立於礼,成於乐”联通解读,认为上一章是孔子教弟子之法,下一章“民可”二句是孔子教弟子法的具体化——弟子优秀者如七十二人在孔子的教导下, 能兴、能立、能成,也即“可使知之者也”;自七十二人之外的众弟子,尽管孔子也以诗书礼乐教之, 但不可能使他们“知道”,他们即是“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民。其结论是:“先王教民,非概不使知者。故家立之塾,党立之庠,其秀异者,则别为教之,教之而可使知之也;若其愚者,但使由之,俾就于范围之中,而不可使知其义,故曰‘君子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4—299-300)刘宝楠的这种二分法显得很是曲折而不免牵强。他之所以不惜牵强地曲折解说,其实是因为感到“以民为群下之通称,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先王教民之定法”的说法有“愚民”之嫌,所以他强调“先王教民,非概不使知也”,于是将民区分为“秀异者”和“愚者”二类从而区别对待。如此折中调停,当然并未能解决问题。所以程树德《论语集释》批评道:“此说以民指弟子,终觉未安。”(5—687)程树德自己的意见则是:“愚谓《孟子·尽心篇》:‘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众’谓庸凡之众,即此所谓民也,可谓此章确诂。纷纷异说,俱可不必。”程树德之见其实比刘宝楠之说更成问题——刘氏把民分为可使知与不可使知两类而区别对待,程树德则以为庸凡的众民统统愚不可及,眼光真够“高大上”的!
晚清以来西方的民权思想自传入中国,孔子的这两句话因为有“愚民”的嫌疑,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议。诚如严复1913年在一次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专题讲演中所说,“今案此章圣言,自西学东渐以来,甚为浅学粗心人所疑谤,每谓孔术胚胎专制,此为明证,与老氏‘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一语同属愚民主义,与其平日所屡称之‘诲人不倦’语矛盾参差,不可合一,此其说甚似矣。”但严复不同意“专制-愚民主义”的批判。他认为:
特自不佞观之,则孔子此言,实无可议,不但圣意非主愚民,即与“诲人不倦”一言,亦属各有攸当,不可偏行。浅人之所以横生疑谤者,其受病一在未将章中字义讲清,一在将圣人语气读错。何以言之?考字书,民之为言“冥”也,“盲”也,“瞑”也。荀子《礼论》有云:“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可知此章“民”字,是乃统一切氓庶无所知者之称,而圣言之贯彻古今者,因国种教化,无论何等文明,其中冥昧无所知与程度不及之分子恒居多数。苟通此义,则将见圣言自属无疵。又章中“不可”字乃术穷之词,由于术穷而生禁止之义,浅人不悟,乃将“不可”二字看作十成死语,与“毋”、“勿”等字等量齐观,全作禁止口气,尔乃横生谤议,而圣人不得已诏谕后世之苦衷,亦以坐晦耳。[10]
看得出来,严复坚持的仍是“民愚”不可教化说,只是补充说“不可”并非孔子主观上禁止教民之义,而是孔子有感于客观上“民愚”难以教化之苦叹。这还是曲意回护孔子之词。
当此之际,托古改制的康有为也曾为孔子辩护。他在1902年所著《论语注》里说:
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深忧长叹,欲人人明道。若不使民知,何须忧道不明,而痛叹之乎?愚民之术,乃老子之法,孔学所深恶者。圣人遍开万法,不能执一语以疑之。且《论语》六经多古文窜乱,今文家无引之,或为刘歆倾孔子伪窜之言,当削附伪古文中。[11]
如所周知,康有为对儒先之言多是“六经注我”地强就己说,说不通处就斥为古文家
刘歆之作伪,一棍子把原著打死。如此主观主义的思想态度,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梁启超很可能看过康有为《论语注》的手稿,对乃师的颟顸主观之论不以为然,而思有以救正之。所以,梁启超不久就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则题为《孔子訟冤》的读书笔记,假设“怀疑子”与“尊圣子”二人论学,其中也讨论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两句:
怀疑子曰。《论语》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语与老子所谓法令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有何异哉。是孔子惧后世民贼不能罔民而教猱升木也。夫文明国者。立法之权。皆在于民。日日谋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之普及。而孔子顾以窒民智者为是。何也。尊圣子云。此子误断句读也。经意本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言民之文明程度已可者。則使之自由。其未可者。則先使之开其智也。夫民未知而使之自由。必不能善其后矣。使知之者。正使其由不可而进于可也。怀疑子无以应。[12]
把梁启超的句读换算过来,则他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断句即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断句真是别开新面,其解释“言民之文明程度已可者。則使之自由。其未可者。則先使之开其智也”也颇为通达。只是把“由”解为“自由”不免时髦了些。
应该说,梁启超的重新断句比他的新解释更富启发性,颇有“解放思想”的意义。从此至今,一方面,“民愚”和“愚民”之争仍在延续,但不论持“民愚”不能教说还是“愚民”不可教说者,都是以传统的句读为依据,所争只在如何解释,谁也说服不了谁,兹不赘述;另一方面,在梁启超的新断句启发下,更新的断句不断涌现。据赵友林的《百余年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阐释考》所述,迄今关于《论语》这一章的断句已有18种之多,大多数是改革开放以来新增的,有不少是脑洞大开的想当然之断。诚如赵友林归纳的那样:
其中得到学者呼应、影响比较大的有以下3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他句读往往附和者寡。在对“民可”句进行探讨时,句读问题常常与主旨问题相互交错纠缠,从而使得“民可”句的探讨更加纷纭复杂。从总体上看,这些探讨丰富了“民可”句的内涵和句读形式,但有些说法过于求新立异,往往缺少文献的支持和严密的论证,显得过于随意。[13]
我同意赵友林的归纳,只是他对这三种影响比较大的断句未加轩轾,显得过于谨慎了。
窃以为,第一种断句也即传统的点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肯定不合孔子的一贯思想,那其实是前人好顺着辞气点读语句的习惯所导致的误断,后来的种种误解和曲说都因这个点断之误而生,理应纠正了。第二种断句也即梁启超点读之改进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间的逗号改为分号),诚然有助于纠正孔子主张专制-愚民主义的误解,但诚如杨伯峻所批评的,“恐怕古人无此语法。若是古人果是此意,必用‘则’字,甚至‘使’下再用‘之’字以重指‘民’,作 ‘民可,则使 (之)由之,不可,则使(之)知之’,方不致晦涩而误解”。(7—81)对杨伯峻的这个批评,我想做一点补充:在先秦两汉的古文中,单用“可”作谓语者并不是没有,但那一定是承前省掉了实动词或宾语,可《论语》此章则并非如凌鸣喈、刘宝楠所谓是与《泰伯》篇的上一章“子曰:兴於诗,立於礼,成於乐”相关联者,而是独立的一章,则“可”欠缺了承前省,是不能单独做谓语的,所以梁启超的断句在古汉语句法上确实不能成立。于是,剩下的第三种断句就几乎成了唯一说得通的选择。
第三种断句是这样的: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我对此章的断句正是如此,原以为这只是自己的想法,直到最近为写这个小文而检索文献,看到赵友林的综述文章《百余年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阐释考》,才知道这样的断句早已有人先发。据赵文所述,“持这种断句法的学者,先后有八十年代的王承璐、陈金粟、宋占生和九十年代的梁颖、吴丕、陈乐平、刘章泽、吴全权、商国君等。”真惭愧自己的孤陋寡闻,当然也很高兴“吾道不孤。”这些学者们各有理据,赵文已有叙述,兹不赘述。
依我的体会,《泰伯》篇的这段话反映的是孔子对教民和使民关系的看法。孔子是志在从政也确实从过政的人,即使他有阶级偏见,也知道执政者不可能单独自为而必须“使民”,所以他也很“重民”的。且看《论语》的《学而》篇记孔子之言:“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颜渊》篇记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宪问》篇记孔子之言:“修己以安百姓。”《公冶长》篇记孔子之言:“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此外,《颜渊》篇记孔子弟子有若对鲁哀公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尧曰》篇引周武王之言:“虽有周亲,不如仁人。……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这些都应是来自孔子的传教,足见孔子很“重民”也很注意“使民”分寸的。当然,执政者“重民”、“使民”,可民众并非天然可用,这就需要先行“教化”即“教民”的,而孔子不仅自己坚持“有教无类”,而且确有“教民”的主张。《子路》篇记载孔子在卫国看到百姓很多,冉有请教夫子:“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答道:“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答道:“教之。”同篇又记:“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诸如此类,都证明孔子是很重视“教民”而“使知之”的,哪有什么“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思想!
并且,要“使民”必先“教民”也是孔子所深知的历史经验。《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左传》是孔子同时人左丘明为《春秋》所撰之传,孔子赞同左丘明的话——“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就出自《论语·公冶长》。也因此,孔子拿《春秋》来教学生的时候,也可能会参考左丘明的传吧。即使孔子看不到左丘明所做的传,他也肯定知道《左传》所记载的三个著名的要“用民”必先“教民”的故事。一是《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补记晋楚城濮之战前三年(即僖公二十四年),“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14]二是《左传·襄公三十年》记郑国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15]晋文公和郑子产的功业和遗爱,孔子是熟悉而且赞赏的。此外,孔子当世的最大时事看点乃是吴越争霸。《左传·哀公元年》记伍员警告吴王夫差:“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16]所谓“教训”即教育训练民众,后来越王勾践果然如此“教训”、终于在孔子去世不过四年就灭了吴。孔子生前熟知或亲闻的这些大事变,对他当然都是宝贵的历史经验,使他深切地明白要“使民”必得“教民”的道理,故而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论。
再者,“民可使由之”里的“由”与“使”其实是同义词,只是由于前面已经用了“使”,后文为了不犯重,故而改用“由”,而“由”的古训恰为“用”,正与“使”字异而义同。“知之”当然可以看成使动用法,但“知”也可以解成为政者对民众的主动教化。仔细体味本章的语气,“使”、“知”其实都暗含着临民者的某种主动性。并且诚如一些旧注所言,民亦不可一概而论,固然有水准高的,不教即堪用,自然也有水准低的,则教而用之可也。另,揣摩夫子语气,前后两“可”字意味也有所不同,前者固“可”矣,后者偏“能”也。这样一来,“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章,似乎可以简洁地翻译成下面的白话——
孔子说:老百姓可以使唤的,就使唤他们;不能使唤的,就教化他们。
顺便也说说《子罕》篇的“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章。此章至迟自郑玄就训读为一句。[17]何晏《论语集注》显然考虑到贬义的“利”与“命”“仁”不相匹配,于是特别解释说:“利者,义之和也”。(转引自1—218)皇疏谓:“利是元亨利贞之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理玄绝,故孔子希言也。命是人禀天而生,其道难测,……故孔子希说与人也。仁是行盛,非中人所能,故亦希说许与人也。”(1—218) 邢疏与皇疏略同。这些注疏都曲顺句读而不得不增字解经。到朱子的《论语集注》,才撤销了对“利”的高调解释,转而采引程子之说:“程子曰:‘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3—109)这样解释“利”是符合孔子和《论语》实际的,但程、朱仍坚持孔子罕言命与仁,那又显然不合孔子的实际。
直到元人陈天祥才看出问题之所在,乃有破有立道:
若以理微道大则罕言,夫子所常言者,岂皆理浅之小道哉?圣人于三者之中所罕言者,惟利耳,命与仁乃所常言。命犹言之有数,至于言仁,宁可数邪?圣人舍仁义而不言,则其所以为教为道、化育斯民、洪济万物者,果何事也?……说者当以“子罕言利”为句。“与”,从也。盖言夫子罕曾言利,从命从仁而已。(转引自5—730)
从此学人才开始意识到此章的传统句读可能有误,而渐渐改变看法。到了现当代,不少学者都接受了陈天祥“当以‘子罕言利’为句”的意见,只是现当代学者们对其后的“与命与仁”,或主张进一步断开为“与命,与仁”,或认为应该四字统断为“与命与仁”,这分歧无关紧要。对“与”字的解释,则趋向于恢复“许与”的古训,而在白话翻译中则用更现代的“赞许”、“赞同”之类。如钱穆的《论语新解》就将“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翻译为:
先生平日少言利,只赞同命与仁。
这翻译简洁得当,意思也很容易理解,切合《论语》的语境整体和孔子的思想实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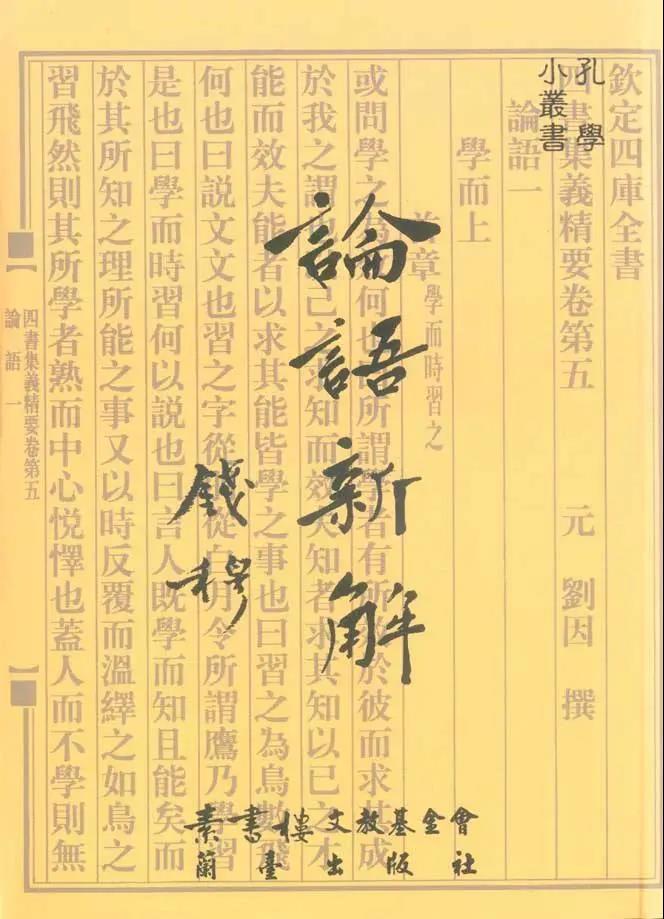
4.“小人哉樊须也”、“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之真意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出自《子路》篇。
此章记言记事很完整,没什么难懂的。唯一的难题是“小人哉樊须也”一句里的“小人”该怎样理解。皇疏以为:“小人是贪利者也,樊须出后,孔子呼名骂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樊迟在孔子之门,不请学仁义忠信之道,而学求利之术,故云小人也。”(1—251)这是直斥樊迟为贪利小人,并引孔子关于君子小人的名言为据,因此成为最常见的解释。邢疏受何晏《论语集解》所引包咸注“礼义与信足以成德,何用学稼以教民乎”的启发,乃谓:“此章言礼义忠信为治民之要。樊须请学稼者,……弟子樊须请于夫子学播种之法欲以教民也。……孔子怒其不学礼义而学稼种,故拒之。……樊迟既请而出,夫子与诸弟子言曰:‘小人哉,此樊须也。’谓其不学礼义而学农圃,故曰小人也。”(2—418)这至少澄清了樊迟请学稼不是为了个人获利而是“欲以教民”,只因“礼义忠信为治民之要”,所以孔子对请学稼请学圃的樊迟有点恨铁不成钢,乃怒骂他是“小人”。对此“小人”,邢疏没有解释。俞樾《群经平议》说:“古书言君子小人大都以位而言,……后儒专以人品言君子小人,非古义也。”[18]按《尚书·无逸》记“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19]则“小人”就是种田的农夫小民。这或者就是邢昺不加解释的“小人”之古义。朱子《论语集注》对小人无注,只引了程门高弟杨时的解说:“杨氏曰:‘樊须游圣人之门,而问稼圃,志则陋矣,辞而辟之可也。待其出而后言其非,何也?盖于其问也,自谓农圃之不如,则拒之者至矣。须之学疑不及此,而不能问。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复。及其既出,则惧其终不喻也,求老农老圃而学焉,则其失愈远矣。故复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3—143)由此可知杨时和朱子都视樊迟为“志陋”学农学圃之小人。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一面解释“小人即老农、老圃之称。……若士之为学,则由成己以及成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当志于大人之事,而行义达道,以礼义信自治其身,而民亦向化而至,安用此学稼圃之事,徒洁身而废义哉!”一面又认为“当春秋时,世卿持禄,废选举之务,贤者多不在位,无所得禄,故樊迟请夫子学稼、学圃,盖讽子以隐也。”(4—524-525)如此一来,樊迟乃是借请学稼请学圃来暗示孔子应该隐居避世的,则樊迟倒是有高远之思,夫子骂他是农夫小民,似乎骂错了啊!清毛奇龄、宋翔凤等都不满杨时对樊迟的贬斥和对学稼的贬低。如毛奇龄《四书改错》痛批杨时之说、为樊须辩护道:“汉儒原云迟思以学稼教民,盖惧末治文胜,直欲以本治天下,一返后稷教民之始,其志甚大,惜其身沦于小民而不知也。此迟有大志而夫子抑之,且仍以大者告之。”(转引自5—1160)此后,对“小人”的解释便分道扬镳:一些人坚持势利小人之贬义,一些人则坚持草野农夫小民之古义,至今如此,莫衷一是。暗用前说者如杨伯峻的《论语译注》,直译“小人哉樊须也”为“樊迟真是小人!”(7—135)采用后说者如钱穆的《论语新注》,乃将“小人哉樊须也”译为“真成一个在野小人了,樊迟呀!”钱穆并解释说:“孔子非不重民食,然学稼学圃,终是小人在下者之事;君子在上临民,于此有所不暇。”(8—243)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则把所有“小人”不加区分地原文照搬。
说来可笑,“文革”后期我上中学,正碰上批林批孔运动,《论语》的这一章成了孔子的大罪状,是那时几乎人人皆知的孔子“反动言论”,我这个农家小子当然也很气愤孔老二怎么能把想学稼学圃的樊迟贬斥为“小人”呢?那不是赤裸裸的阶级偏见么!后来上了大学,才知道“卑鄙小人”说和“草野小民”说的来历。此后读到《论语》全书,自己玩味体会此章语境和孔子的语气,渐渐觉得以上两说都不甚切合上下文的语境也不一定合乎孔子的原意。一则孔子是个一向待人和气的人,在教育上也始终坚持“有教无类”、“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这样一个好教育家的孔子,怎么会因为樊迟提了两个不合宜的问题,就斥骂他是卑鄙贪利之小人呢?并且,如果樊迟真是个卑鄙势利之小人,孔子还会让他继续当学生吗?可是,我们看到孔子与樊迟的师生关系,并不止于请学稼、请学圃一节,其实直至孔子终老,樊迟都是孔子的学生,他给孔子驾车,向孔子请教其他问题,如“樊迟问政”、“樊迟问仁”,孔子都很耐心回答,夫子还主动为他讲孝,如此等等,都说明樊迟始终是孔子承认的学生,其身后也名列“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和《仲尼弟子列传》之中,这些怎么解释呢?二则,孔子诚然有阶级等级观念,但那只是就客观的社会差别而言,孔子在主观上并不势利取人,他更赞赏的是人的德行而非等级出身,他也没有瞧不起下层劳动者,他自己就坦承“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路》),所以孔子才会接受贫贱的仲弓为弟子——仲弓父,贱人,夫子却赞赏说:“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雍也》)即就本章而论,孔子也并没有瞧不起老农老圃,他只是老实承认在为稼为圃的事务上自己不如老农老圃。然则,夫子又怎么会因为樊须请学稼请学圃,就毫无道理地迁怒于农夫、以至于轻蔑地斥骂樊迟是如农夫一样的“草野小人”呢?诸如此类的疑问,让我渐渐感到两种通行的“小人”说,不仅对樊迟固然言重了,而且也都在无意中给孔子戴上了势利眼镜,所以都未必妥当的。
然则,还有没有比较切合本章语境和孔子真意的理解呢?有的,其实还有一种不很流行的看法,来自金人王若虚。王若虚认为《论语》中的“小人”别有一种意义:“其曰‘硜硜小人’、‘小人樊须’,从其小体为小人之类,此谓所见浅狭,对大人而言耳。”[20]王若虚的意思是说,《论语》中也有一种“小人”的用法,指的是体小之人、引申为见识浅且固执之人,乃与成熟有见识的大人相对而言。换言之,这等“小人”也即我们今日所谓年龄不大、思想幼稚、不很成熟的年轻人。这给我很大的启发:虽然樊迟是否长得“体小”,不得而知,但他向孔子“请学稼”的时候,很可能比较年轻幼稚、思想单纯吧,这或许就是孔子在此章中所谓“小人哉樊须也”之真意,略同于《论语》中也有的“小子”之意。史载樊迟“少孔子三十六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其从学于孔子是比较晚的。本章所记很可能是樊迟初随孔子学习时候的事情。那时还很年轻的樊迟不免思想幼稚,他不明白孔子所教的乃是不能从日常生活里自然学到的礼义文化传统和从政理民之道,而误以为夫子什么都能教,于是向他请学稼、请学圃,他不知道稼与圃之类农事原本是农人父子兄弟之间自然传授的生产经验,他用不着到夫子那里专门去学这些,孔子自然也不能且无法教他这些,所以夫子只能以“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来婉拒。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从整部《论语》关于樊迟的记述来看,他不像颜渊、子张那样聪明过人、可以举一反三,而是一个反应比较迟钝、思想比较朴直的年轻人。从《为政》篇记孟懿子问孝一章就可以看出,樊迟的反应确实有点慢、接受能力也是比较差的,饶是孔子多么循循善诱,樊迟还是不能理解,孔子不得不对他耳提面命: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
同样的迟钝反应,也出现在本章中。如上所说,孔子所教的是礼义文化传统和从政理民之道,至于稼与圃之类农事知识,原是农人父子兄弟之间自然传授的生产经验,孔子哪能教樊迟稼圃啊,他就是想学稼圃也不必来向孔子学啊——这些孔子自然不便向樊迟明说,怕挫伤了他,只能委婉推诿道:“吾不如老农。”可是樊迟还是那么天真,没有明白孔子推诿的意思,仍然固执地继续向孔子“请学圃”,这让孔子很无奈,只能又一次推诿道:“吾不如老圃。”两次碰壁之后,樊迟只能怏怏而退。孔子乃感叹道:“樊迟真是个幼稚的小子啊!在上者崇尚礼,老百姓不敢不尊敬他,在上者崇尚义,老百姓不敢不服从他,在上者崇尚信,老百姓不敢不用真情对待他。如此教化行政,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背着孩子来跟从的,哪里用得着教他们种庄稼啊!”这些道理在场的其他弟子都懂,可天真迟钝的樊迟就是不明白,难怪孔子要感叹“小人哉,樊须也!”即“樊迟真是个幼稚的小子啊!”不难体会,夫子此言中感叹与嗔怪兼有,若理解成贬斥、怒骂樊迟,那就过分了,既非樊迟所应受也非夫子所宜言。
我觉得,这样理解“小人哉樊须也”,既合乎此章的语境,也比较符合孔子和樊迟的关系。我当过二十年学生又做了三十多年老师,在同学和学生中不止一次碰到过类似樊须这样天真单纯而其实忠厚朴直的人,他们并非“朽木不可雕也”的蠢才,只是开窍晚点而已,遇到好老师的启发,迟早会成才的。樊迟的遭遇正是这样,孔子并未因他天真幼稚就弃他于不顾,仍然耐心地回答他的问题、细心地点拨他,终于有一天樊迟开窍了,问的问题非同一般: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论语·颜渊》)
樊迟能提出这样有深度的问题,说明他是真开了窍、会思想了,所以孔子高兴地夸奖他“善哉问!”并且很愉快地回答了他的问题。这提醒我们,在解读有关各章时,应考虑到孔子与樊迟师生关系中的这些复杂曲折的情况,给予入情入理的解释,而非孤立的说文解字。
相似的问题也出现在《阳货》篇的“女子与小人”一章里: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此章除了“小人”问题,还涉及“女子”问题,历来解释多从男尊女卑着眼,所以到了近现代,便成了孔子歧视妇女的铁证而备受非难。汉魏古训已不可见,只有《后汉书》杨震传载其上书汉安帝:“夫女子小人,近之喜,远之怨,实为难养。《易》曰:‘无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与于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伯荣,莫使往来,令恩德两隆,上下俱美。”[21]原来汉安帝放纵乳母王圣及其女伯荣,所以杨震上书劝其赶走阿母、断绝伯荣,为了说服安帝,杨震乃暗用《论语·阳货》此章、明引《易经》的“家人”之卦,自不免断章取义,不足为据。《论语集解》的皇侃疏乃谓:“女子小人并禀阴闭气多,故其意浅促,所以难可养立也。‘近之则不逊’者,此难养之事也。君子之人,人愈近愈敬,而女子小人,近之则其承狎而为,不逊从也。‘远之则有怨’者,君子人若远之,则生怨恨,言人不接己也。”(1—289)这显然是从阴阳尊卑上看待女子,并视“小人”为君子小人对立意义上的“小人”;“小人”通常为男性,却也被打入“阴”的范畴。如此曲折解释是很勉强的。邢疏则谓:“此章言女子与小人皆无正性,难蓄养。所以难养者,以其亲近之则多不孙顺,疏远之则好生怨恨。此言女子,举其大率耳。若其禀性贤明,若文母之类,则非所论也。”(2—460)这显然是有鉴于皇疏贱视所有女性、有一棒子打死之嫌,《诗经·大雅·思齐》不也歌颂文王的母亲太任、祖母太姜及妻子太姒之贤德吗,所以邢疏特为这类“禀性贤明”的女性网开一面。朱子的《论语集注》也缩小了“女子”、“小人”的打击面,以为“此小人,亦谓仆隶下人也。君子之于臣妾,庄以涖之,慈以蓄之,则无二者之患矣。”(3—182)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认为“此为有家国者戒也。养犹待也。”然后广引史传以至《易经》为君子远女子小人作证,传统得更有来头。(4—709)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汇集旧注,然后引明人冯从吾的《四书疑思录》和清人汪绂(初名汪烜)的《四书诠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四书疑思录》:‘人多加意于大人君子,而忽于女子小人,不知此两人尤是难养者,可见学问无微可忽也。’《四书诠义》:‘此言修身齐家者不可有一事之可轻,一物之可慢,毋谓仆妾微贱,可以惟我所使,而忽以处之也。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而礼必本于身,以惠爱之心,行天泽之礼,乱本弥矣。所以庄以涖之,慈以蓄之也。君无礼让则一国乱,身无礼则一家乱,女戎宦者之祸天下,仆妾之祸一家,皆恩不素孚,分不素定之故也。夫子言之,其为天下后世虑者至深且远也。’”(5—1603)这实在是迂腐刻深的礼教-道学之解。
也因此,新文化人对孔子此言均持严厉批判态度。如吴虞就指斥道:“孔学对于女子,尤多不平。……孔子既以女子与小人并称,故视妇女为奴隶,为玩物,主张多妻制。……此不佞所以不能不非孔也。”[22]鲁迅更讥嘲孔子道:“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 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23]左翼学者蔡尚思则批评孔子道:“既认女子全是小人,就可想见男人全是君子了。……孔子的主观片面,竟到如此地步。”所以他斥责孔子“是女性的敌人,男性的恩人。”[24]现代学者则多因循旧注而回避问题,如钱穆的《论语新解》仍沿袭朱子之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则不加注释而只有译文:“孔子道:‘只有女子和小人是难得同他们共处的,亲近了,他会无礼;疏远了,他会怨恨。’”这译文仍然采信传统的解释。李泽厚一方面确认孔子“这句话相当准确地描述了妇女性格的某些特征。对她们亲密,她们有时就过分随便, 任意笑骂打闹。而稍一疏远,便埋怨不已。这种心理特征本身并无所谓好坏,只是由于性别差异产生的不同而已;应说它是心理学的某种事实。”另一方面,秉持现代观念的李泽厚又不能不批评孔子此言确有偏见:“至于把‘小人’与妇女连在一起, 这很难说有什么道理。自原始社会后, 对妇女不公具有世界普遍性, 中国传统对妇女当然很不公平很不合理, 孔学尤然。”[25]这给人奇怪的感觉:新旧论者立场不同却看法相似,看来孔子对女性的偏见已无可怀疑了。
新时期以来,学术界也有人出来为孔子此言做辩护,辩护者多从训诂标点入手重新解释孔子此言的意义,由此出现了一些新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廖名春。他认为“女子与小人”中的“与”当训“如”,“与小人”就是“如小人”,且“与小人”乃是“女子”的后置定语。如此缩小了“女子”的范围,进而解释全句道:“《论语》此章的‘女子与小人’是一个偏正结构,‘女子’是中心词,‘与小人’则是后置定语,是修饰、限定‘女子’的。因此,这里的‘女子’不可能是全称,不可能是指所有的女性,而只能是特称,特指那些‘象小人一样’的‘女子’,‘如同小人一样’的‘女子’。这种‘女子’‘如同小人’,其实质就是‘女子’中的‘小人’,就是‘女子’中的‘无德之人’”。原来孔子此言只是就一些如小人一样的坏女人而言,并没有全然否定妇女的意思。廖名春于是宣告:“‘五四’以来藉《论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章攻击孔子极端仇视妇女,‘是女性的敌人’的说法可以休矣。”[26]应该承认,廖名春之论用心良好,但他解“与”为“如”以及“与小人”为“女子”的后置定语之新说,实在迂曲得很,不免强为之说。此类新异的训诂还有不少,大都不足为训,兹不具引。
其实,孔子固然未曾高看女性,却也未必轻看女性,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没来由的轻视之谈?检点以往对“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解读,有两点是说不通的:一是此句中的“养”被解读为“蓄养”,然则蓄养“女子”,还勉强可解成古人养小妾或如今日养小三之类,男人既然好这一口,也就只能忍耐女子的任性了,可是令人不解的是,人干嘛要“养小人”,那不是没事找事、自找麻烦吗?且“小人”既不好养,则赶走便罢,为何却在“近之”“远之”之间纠结不下,似乎无可奈何、不养还不行——这说得通吗?二则此句所言“女子与小人”的毛病,也不过“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而已,这实在不是多大多严重的原则问题啊,然则孔子竟然会因为这么点小问题就贬斥“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不是过甚其辞么?可是从全部《论语》看,孔子说话论事一向很通情达理也很有分寸的,他并不是一个前言不搭后语的糊涂人、更不是一个出言夸张过甚其辞的人啊!
正是这两个说不通的问题,让我怀疑向来对孔子此言的解读大多是想当然的望文生义之论,而忽视了孔子此言的具体语境和特定针对性。前面说过,《论语》中的有些语句实在过于简略,加之编辑成书的时候,各章之间也不一定有事实上的或逻辑上的关联,语境不很清楚、意义颇难寻味。但所幸“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不在此列。仔细揣摩一下,此章的具体语境和特定针对性还是可以把握的,而解读的关键是必须把“女子与小人”、“养”和“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联系起来,因为它们是一个意义连贯的整体,只有弄清它们之间的关联,才能明白孔子此言的语境、针对性及其确切的意义。
首先,这段话中的“女子”不是指所有女性,而是特指女儿。按,在先秦之时“女儿”也可简称为“子”,如孔子同情学生公冶长无辜遭罪,便“以其子妻之”,即把女儿嫁给了公冶长,这里的“子”就是女儿的意思;如果为了与儿子区别,则可复称为“女子”,如《诗经•小雅·斯干》:“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这诗句里的“女子”就指女儿。“小人”则如上说“小人哉樊须也”之所言,不是概指品德不好的“小人”,而是指年纪比较小、思想比较幼稚的男孩,即“小子”、“小儿”的另一种说法。如此,则此章中相并列的“女子与小人”指的就是女儿和儿子,并且是年纪较小的还在少女少男阶段的女儿和儿子。然后,看句中“难养”之“养”,绝不可能是“蓄养”仆妾之“养”,而只能是“养育”孩子之“养”。最后再寻味全句所感叹的问题,的确是为父母者比较头疼的难题——父母养育年少的女儿和儿子,都会感到为难的问题是什么?不就是与子女关系远近亲疏的分寸不好把握吗?所以夫子慨乎言之:“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即跟孩子们过于亲近,他们就不免顽皮放肆,没大没小的,对他们端起为父为母的架子,不甚溺爱而有点距离,以便严格要求他们,则孩子们又会嫌父母疏远而心生怨气。这委实是千古不易的养育子女之难题。教育家孔子也是有儿有女的人,而教育家往往可以教育好别人家的孩子,却无法处理好教育自己子女的问题,其难处就在于,自己同时作为父母和作为教育者的双重身份不好协调,跟孩子太亲近了不行,太远了也不行,分寸怎样才算恰当是很难把握的。孔子身为父亲,在教育自己孩子的问题上自然也难免这种苦恼,所以才有了这句深有体会、颇感无奈的感叹:“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把这句话译成白话,大意如下:
孔子感叹道:姑娘和小子都不好养育啊。跟他们亲近些吧,他们就调皮得没大没小,与他们疏远一点吧,他们又会心生怨气。
同时还应注意,孔子此言也反映了青少年的心理特点。今天的人们都知道,少男少女们正处在尝试建构自我认同的阶段,多少都有点叛逆性,与父母的关系若即若离的,让父母不免为难。孔子之所以感叹养育孩子不易,尤其是与孩子关系的远近分寸不易把握,其实也是因为他发现了子女在这个成长阶段必有这样难调的问题。尽管那时的孔子不会有现代的青少年心理学知识,但他身为父亲又是个经验丰富的教育家,对子女教育问题的特殊困难,当然会有切身的感受和细心的观察,因而才会对人(可能是与老学生们闲聊时说起吧)发出如此深有感触的感叹,我们千载之后读来,仍然能够体会到孔子作为父亲的爱心和无奈。关于孔子女儿的情况,文献记载很少,我们不好推测。儿子孔鲤的情况,《论语》则有所记载,从中可以看出,半大小子的孔鲤对父亲孔子的确有点敬而远之,倒与孔子的学生如陈亢等人的关系较为亲近。因此,陈亢有一天便好奇地探问孔鲤,作为父亲的孔子是否给他开过小灶: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论语·季氏》)
从孔鲤的回忆里可以感受到,孔氏父子对彼此有都点小心翼翼,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微妙距离,而陈亢由此得出“君子之远其子也”的结论,可能是皮相之见。其实,孔子未必有意“远其子”,他只是对一个有意趋避他的儿子无可如何,只能逮住机会就叮嘱他一句,而孔鲤唯唯诺诺地答应了,便赶紧走开——在孔子这个父亲面前,孔鲤大概也觉得有些压抑吧!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得不面对这样有些尴尬的父子或父女关系。我与女儿的关系就是这样。所以读“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真是亲切得感同身受。
余论:孔子、康德与道德的普遍性问题
恰在写这篇小文的过程中,2019年6月12日的“凤凰网国学”刊出邓晓芒教授新著《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句读》的出版发布会消息,以及邓晓芒与另外两位教授关于“康德及康德道德哲学三人谈”,所谈的核心问题乃是孔子与康德在建立道德普遍性标准上的区别——按邓晓芒的话说,那差别便是:“孔子没有建立普遍的道德标准,而康德提供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应该承认,至少在哲学的某些领域如本体论、认识论上,略晚于孔子的西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思辨的深度、逻辑的严密,就远非孔子所可比拟了,遑论两千年后的康德、黑格尔!但说到伦理学或道德哲学,那就另当别论了。康德治道德哲学或伦理学,仍然沿袭着他研究认识论所遵循的路径,诉诸人类的理性认识,运用严密的逻辑推衍,经过苦心孤诣的思辨,终于得到三条普遍的道德原则,乃以为道德律大成、永世无可违。但其实,道德的达成并不取决于人的认识而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可人的自由意志究竟如何能让人必然地行事道德、绝对的道德命令究竟如何能令人非如此不可地践行不殆?康德就理屈词群而无能为力了。此所以纵使人能认识到道德的普遍性,人的行为却未必都能遵循这种普遍性。正唯如此,康德的伟大道德律并不能阻止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做出丧尽天良的背德恶行。孔子诚然不擅长玄深的思辨,却比康德更早也更深切地洞察到认识未必有助于道德,所以孔子并不追求由认识来获得普遍的道德原则,而相信道德来源于人性的觉悟——正是人性的觉悟让人将心比心,做出合乎人性的道德行为——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仁由己”、“当仁不让”,诸如此类的孔子道德经验之谈也只对有人性的人类而言,并且总是关联着具体情境,因而对不同时代却可能遭遇相似境遇的人产生亲切的感召力。这就是孔子道德言论的具体普遍性,它比康德经由思辨所得到的道德普遍性更近于人也更具感召力——“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所以孔子的道德言论影响于人的德行之广泛和深远就远非康德所可比拟。也因此,邓晓芒教授为孔子在康德面前感到惭愧,实在语无伦次。其实,真该惭愧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距康德也有二百年了,早该追问康德的道德哲学未能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倘若人的自由意志并不能必然使人向善,倒有可能使人欣然作恶,甚至以恶为善,如曹操所谓“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或俗谚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则对道德的论理普遍性之认识究竟如何才能落实为人的伦理实践的必然性?伟大的康德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邓晓芒教授若能想想辙,则幸甚至哉。
2019年6月27日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本文原文分上中下三篇,连载于《名作欣赏》2020年第4期、第5期、第6期,经由解志熙教授授权发布。
注释:
[9]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937页(第三册),中华书局,1994年。
[10]严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兹据《严复集》第2册第326—327页,中华书局,1986年。
[11]康有为:《论语注》第114页,中华书局,1984年。据康氏自序,此书撰成于1902年春3月17日。
[12]梁启超:《孔子讼冤》,原载《新民丛报》第捌号,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十五日,日本横滨。
[13]赵友林:《百余年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阐释考》,《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10輯,2018年3月。
[1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47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
[1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182页,版次同上。
[1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066—1067页,版次同上。
[17]参阅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第104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18]俞樾:《群经平议》,此据王先谦编《皇清经解续编》第5册第1201页,上海书店影印,1988年。
[19]此引《尚书·无逸》据《十三经注疏》本第221页,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
[20]王若虚:《<论语>辨惑·二》,《滹南遗老集》 第33页,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新1版。
[21]王先谦:《后汉书集解》第615页,中华书局,1984年。
[22]吴虞:《对于祀孔问题之我见》,《大夏季刊》第1卷第1期,1929年5月1日出刊。
[23]鲁迅:《关于妇女的解放》, 《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第5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 第194页。
[24]蔡尚思:《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棠棣出版社1950年出版),此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0页。
[25]李泽厚:《论语今读》第309页,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
[26]廖名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疏注及新解》,《人文杂志》,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