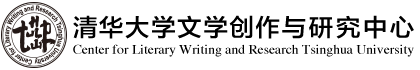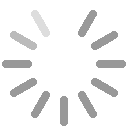“丝绸朋克”之路——刘宇昆对话吴岩
2017.11.16
2017年11月15日,由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学生会时代论坛共同主办的讲座“‘丝绸朋克’之路——刘宇昆对话吴岩”在西阶梯教室举行,活动由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文系助理教授贾立元主持。对话中,刘宇昆和吴岩两位嘉宾就“丝绸朋克”的概念、中外科幻写作现状等话题展开探讨,现场气氛活跃。以下为对话内容节选。

讲座现场(左起:贾立元、刘宇昆、吴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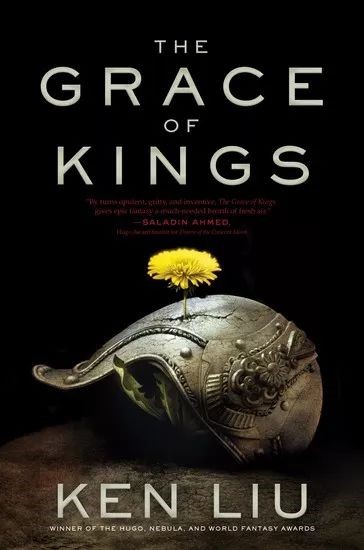
刘宇昆最新作品《七王之战》
对话内容(节选)
贾立元: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是美国作家、翻译家刘宇昆先生,这是中心成立之后第一次邀请国际作家来校。第二位是科幻作家、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吴岩老师。两位嘉宾今天对谈的题目是“丝绸朋克之路”,大家可能觉得好像很神秘。其实,“丝绸朋克”和刘宇昆先生的第一部长篇,“蒲公英王朝”系列第一部——《七王之战》有关,所以我想请他谈一下“丝绸朋克”的概念。
刘宇昆:我是一个懒人。我写作的所有细节,都可以用我比较懒解释,比如你们大家都是上了不同的高校来深造的,我比较懒,第一我上的大学是哈佛,就是“哈哈笑弥勒佛”的意思,也可以说是美国的清华,我去了以后,因为比较懒,不想去看别的学院,所以上了法学院,这是我懒的第一个证据。
“丝绸朋克”这个设想,也是比较懒的设想,因为我当时写长篇小说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有很多不同的作家写出了不同的作品,我要写的话还要看这些小说,还要想写的怎么不同,这个比较麻烦,没有这个精力,所以我的想法是在我在脚下画一个小圈叫“丝绸朋克”,我一个人在里面站着,这样我怎么写就没有人说我写的和别人一样,这是我自己的类型,所以这是我的窍门,先作出这么一个自己的类型,然后一个人在里面做。
“丝绸朋克”是个奇幻小说,一般西方奇幻小说用的是假的中世纪欧洲的背景,所以看起来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要写得比较好玩儿一些,所以就把一些东方和西方的元素合在一起,加入一些机关术,或者演义小说、武侠小说里比较玄的东西,想办法变得真实一下,再夸张一下——奇幻小说就是把可以做出来的东西夸张一下,然后反正也是写小说,又不是真正造这些东西,只要能够在一个数量级上、差不多就可以了——所以我就把一些和中国古代演义里面的相似的东西,放在虚构的世界里,既有东方元素,又有西方元素,然后我把它叫做“丝绸朋克”,这样读者一看就知道,这就差不多了,尽管和真正的中国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谓“朋克”,原意是赋予旧的东西以新的意义,带有反抗性。我的想法是,一般奇幻小说会告诉你:世界是不好的,是乱的,如果有好的国王能够回到他的宝座,所有一切都好了。我不太喜欢这样写,我的奇幻小说里会有不断的反抗,一直是为了创造更好的世界,人物在不断的往前抗争。所以,我想我的小说叫“丝绸朋克”有这么一半的开玩笑的意思,但是也有一半是比较严肃的意思。
我写了自己喜欢写的小说,也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小圈子里,写出来以后觉得还像那么回事儿,还蛮满意的。
贾立元:你出生在兰州,8岁去了美国,兰州就是我们古代丝绸之路上重要的站点。我看到你的访谈说,《七王之战》,融合了不同世界文学的传统,包括中国的《史记》,还有你小时候跟祖母一起听的评书,我想知道,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东西之间的交互,有没有给你什么想象的空间?
刘宇昆:我的想法是可能比较美国化。美国文化有个特点,大家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然后他们把自己的文化带过来变成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美国文化最有趣的是可以看不同作家写的东西,他们经常写的是从世界其他地方来的东西,或者是传说,非洲、日本或者中国都有,但是他们写出来之后都变成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写的小说也是这样,我的小说都是美国小说,都是用这种美国文化融合的方法来处理,可以说美国文化就像大海一样,各种各样的河流流进去,然后可以容纳进来。我想写“丝绸朋克”就是想把奇幻文学里用中世纪欧洲作为背景的现象改变一下。因为我觉得奇幻就是要幻想,想的更加开放一些,可以想出以前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我就喜欢写这种东西方结合在一起,但是非常美国化的写法。不过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和我这种美国文化的解释也相似,也就是把各种不同的传统融合在一起。
吴岩:这个是我特别想和你讨论的问题,因为我有时候见海外的华人作家,因为总有人说你们是东方人,他们就不断地讲,我其实写的是美国作品。你自己感觉是不是这样?就是说你们要不断强调写的不是中国的作品?
刘宇昆:这个是有。我觉得要看怎么解释。如果把这个作品作为中国作品来看的话,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这完全是用美国的视觉来看中国元素,但是我用的时候并不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我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带到美国去的。其他的海外作家我没法评论,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在我看来,我没有特别强调这方面,因为我觉得我在美国的经历和其他很多少数族裔的兄弟很相似,因为在美国很大的问题是白人至上主义,很多人认为美国是一个白人的国家,我觉得很奇怪,事实上当然不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些读者在美国当然会有这种感觉,如果不是从白人文化获取的东西他们就觉得不是美国文化,这是很可笑的一种看法。但是我觉得这种强调没有什么用,因为我自己是美国人,所以写出来是美国东西,不用跟他们强调,而且我是比较懒的人,与其和他们吵架,还不如多写一篇小说,可以让更多的读者来看。
贾立元:丝绸之路推动了古代中国跟西域更广袤的地区在经济上、文化上的交流。今天的中国又提出新的“一带一路”计划,不仅有经济、政治上的考虑,也有增进文明之间互相理解的考虑,我觉得这和“丝绸朋克”的精神相契合。一方面,刘宇昆把他从多种文化中得到的养分融汇到他个人的创作之中,另一方面,就是他对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的精深掌握,使他能够非常出色地将中国当代科幻作品介绍到英语世界里,让它被更多的读者认识。所以,我觉得刘宇昆在幻想文学的领域里,开创了一条“文化丝绸之路”。
刘宇昆:你这个提法很有意思,今天的世界很奇妙,从一种意义上来说,英语其实就是今天的丝绸之路,因为英语是文化交流的载体。我的经验是,很多英文作品翻译成英文之前,很少被非英语国家关注,但是翻译成英语之后就会有很多人来看,因为在欧洲,在乌克兰、波兰、北欧,很多人有很深的英文造诣,他们从小都是双语教育,但很少有人会读中文,所以中文作品翻译成英文之前,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作家写的什么,但是翻译成英文之后就会有很多不同的编辑来和我或者和出版商谈,能不能引进这部作品,来出版西班牙语、俄罗斯语、日语之类的,这是比较奇怪的,就像郝景芳那篇小说,其实翻译成日语的时候他们用的是我的英文原稿,因为他们没有从中文原稿翻译过去,这种事情其实发生了很多次,所以英文会变成像丝绸之路一样的文化交流的。
贾立元:好像《三体》的一些欧洲版也是从英文版翻译过去的。
刘宇昆:是有一些,尽管我的想法还是尽量从中文直接翻译过去,但是在一些欧洲比较小的国家,他们确实没有胜任的译者能直接用中文本翻译。
贾立元: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个科幻小说,故事中的人要研发一种翻译软件,可以在任何两种语言之间翻译,结果发现计算量太大,不可能实现,最后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任何一种语言先译成英语,再把英语翻译成别的语言,这样就大大减少了中间的计算过程。
刘宇昆:对,谷歌翻译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就是用英语作为中介语。
吴岩:你的创作里面既有科幻也有奇幻,但是更多的是奇幻?
刘宇昆: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写的小说只有一个点。我比较喜欢菲利普·迪克的写法。在他那里,科技发展不是他注重的部分,他最喜欢把科学语言作为一个比喻,他想象一个比喻,把它用科技语言变成一个真实的东西,幻想小说都是这样写的,里面东西的幻想元素就是我们平常谈的比喻然后变成真的。就像我写《折纸》:人们常说,你要是爱一个人的话,或者你的世界上充满爱的时候,死的东西就可以有活力,看起来有更加鲜艳的颜色,可以活过来。我就把这种比喻变成真实的,我的小说里就是折纸的动物因为爱活了过来。所以这里的东西不是和科技有太大的关系,只是用科学的语言作为比喻而已。
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我和中国的科幻迷探讨时经常问他们,什么叫“硬科幻”?结果不同人给我的定义非常不同。我问能不能给出一个例子?有人说经典科幻电影都是硬科幻,《2001:太空漫游》、《银翼杀手》。我说这就算硬科幻啊?《2001:太空漫游》最后把外星人比喻成上帝,这是非常基督教中心的东西。《银翼杀手》里的东西,好像根本是用来探讨人与人之间同情、同理心的,和所谓的机器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和一些国外的教授谈《三体》的时候,他们也都说很喜欢这部小说,我说“你知道吗,很多人认为这是硬科幻小说”,他们说“哦,原来这是硬科幻啊。我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硬科幻”的说法没有什么用,因为科幻和所谓科技没有什么关系,你要是真的对科技有兴趣,应该去看科学家的论文。我最喜欢上网站看论文,学一学前沿科技,但是看科幻的时候,我是在看比喻和幻想元素怎么运用。
贾立元:中国很多科幻迷推崇硬科幻,可能因为我们从小就要学科学、爱科学有关系,每个人小的时候都有一个当科学家的梦想。
刘宇昆:那可以去看论文啊。
吴岩:其实中国的科幻很重视科学,现在也有一个观点,所谓的中国科幻和国际上的科幻其实不是一回事。

刘宇昆
刘宇昆:这个很有意思,因为用科幻作为科普的手段,在中国和苏联都有这么一段历史,科幻是作为一种手段,我不能说美国没有这种事情,美国的黄金时代也有一些科幻作家也觉得用科幻教科学是很好的做法。但是问题是你看这些作品里面很多设定都是错误的,这些科幻作家当时也没有太深的科学造诣。所以我的想法是,与其自欺欺人地说自己写的是科普,还不如放弃掉,就说我写的是幻想文学,我对未来是充满憧憬的,但是我其实并不是科学家,我也不懂,我所喜欢写的是用科学语言描述一些我想象的比喻,来推进大家对未来的思想。我来北京之前,在新加坡和香港也开了一些国际作家会议,我们也在谈科幻,其中有一个演讲,题目叫《当幻想变成现实的时候科幻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力?》,讨论的是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很多科幻的东西变成了现实了,科幻作家是不是没有什么可写了?科幻作家怎样才能够想象未来。我的看法可能跟大刘非常不一样,我说一下,你们骂我也可以。
我的看法是,科幻小说对未来的预测从来没有太大的用处,科幻小说中对未来的预测有99%完全错误,就算是偶尔是对的,也是大方向上对的,细节上完全错误,科幻其实对科学的发展没有多少的预测能力。这是为什么呢?我干了很多年的技术工作,以前做专利法和商业秘密的诉讼方面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算是技术发展的历史学家吧,或者说半历史学家。我发现,从科技史的角度来看,科技发展的方向是很难预测的,因为在每个时代,同样的问题都有很多的人在从不同的方向去解决,你很难在当时预测出哪一个方向会有突破,但在十年、二十年后再回顾时,你才看到除了那个突破口之外其他的方向都不可能。就像《黑天鹅》的作者所说:人常有一种错觉,我们经常会把偶然连起来讲一个故事,让历史看起来像是必然如此,但事实并非这样。比如,1900年的纽约街头已经有很多车了,其中大概38%是电动车,爱迪生就是电动车的重要推动者,还有40%的车是蒸汽车,剩下的车才是汽车,如果你问那个时候的人,到底哪一种会在二三十年后成为最重要的技术?肯定很多人说电动车,因为爱迪生在后面推动,他就是当年的特斯拉,是最有名气的发明家。也有人会说,当然是蒸汽车,因为蒸汽是我们用了很多年的技术,是真正受过考验的技术。但是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另外一个例子:有整整30年,很多人都在研究触感屏幕,iphone最后能够成功是非常偶然的。所以,预测技术的发展是非常困难的,如果科幻作家能够预测科技发展的细节,我们就不用做科幻作家了,就去投资好了,肯定变成亿万富翁。但是科幻作家都没有做投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预测不来。
我的看法是,科幻的价值不在于此,而在于给人一种对科技的感觉,让人觉得科学真的很奇怪、很伟大。你看《三体》或者其他科幻小说里面描写的宇宙,觉得宇宙多美好啊!可以发现它的秘密,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这种感觉是科幻很重要的一部分。另外,科幻给你一套探索未来的语言,比如说像《1984》或者《美丽新世界》,当然预测未来没有多大的用处,但是他发明了一套语言,我们可以用这种语言来描述未来,或者威廉·吉普森写的《神经漫游者》,其实吉普森当时对计算机一窃不通,不懂程序员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所以当时做计算机工程的人都很瞧不起这部小说。但是他发明了一套语言,后来的人用这套语言来塑造他们对未来的想法。所以,科幻不能预测未来,但是作为一种语言,作为一套比喻,作为一种系统,让大家来想象未来,我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
吴岩:我想知道你平时都看什么作品?
刘宇昆:我看的东西比较杂,很多是论文,然后还有最高法院发下来的判例,我很喜欢看那些东西。其实这些大法官也是很好的讲故事的人,你看过他的案子,就可以看到他怎么样讲故事,怎么样把证据放在一起,然后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结果。除此之外,我也看非虚构文学的东西,比如游记,或者讲一些经济学或者历史的,各种各样新奇的我不太理解的东西。
吴岩:再问一个问题,我九十年代的时候去美国开一些科幻的会,我感觉人非常多,而且大家觉得是那种火热的感觉。但是这些年我再去,他们自己都说我们是小众,是不是确实有这种状况?
刘宇昆:这个其实很矛盾,你要看美国电影票房最高的都是科幻、奇幻这种类型的电影,但是如果看科幻迷和科幻作家聚在一起的会,确实人不多。我觉得原因很多,比如很多年轻的读者现在看的更多的是漫画之类的,而不是所谓的科幻作品,而且有很多科幻作家转写成主流文学,主流文学里有越来越多的科幻、奇幻元素,而不是按照科幻、奇幻类型文学的标签发表出来。
贾立元: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就是克隆人的故事,但是他不会参加科幻活动的。
刘宇昆:对,很多主流文学作家写的东西有很多科幻元素,但是他们写的不是我们传统上可以划分为科幻文学的这种东西。
贾立元:我觉得中国好一点的地方是,十年前我们参加科幻的活动,来的主要是年轻人,十年后来参加科幻活动的依然是年轻人为主,这是科幻人口再生产的特别好的现状。
刘宇昆:美国作家来到中国都会有这种感觉,中国的科幻迷特别年轻、特别热情,在美国我们开大会的时候不会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在美国开大会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最年轻的一个人,很不可思议。但是另外一个倾向也很奇怪,在美国有很多年轻的科幻作家,每年都有新的科幻作家出来,每年得奖提名的人都是不同的人,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出现。但是我觉得在中国好像没有那么频繁的发现新科幻作家。
吴岩:《三体》写完了以后我就跟刘慈欣说过,你这个做法非常不对:你一直写到宇宙没有了,没有办法再去写了。这是开玩笑了。确实你刚才讲的这件事情真的很有意思,好像从《三体》以后,我们只能《逃出母宇宙》,到别的地方去,新作者的出现可能还需要时间。
贾立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中心要成立——就是要发现年轻的文学人才。回到这个题目上,关于东西文化交流,我们以科幻文学作品作为一个切入点,然后让彼此之间互通有无。当然刘宇昆的工作非常重要,但是也要有像《三体》这样的作品出现,值得被翻译,能够引起跨越语言的共鸣。我想问的是,中国科幻到底给世界科幻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吗?
刘宇昆: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个人的看法可能和很多人不太一样,因为我经常在西方被人问,你翻译了很多中国科幻,你觉得中国科幻和西方科幻有什么不同之处?我回答:第一,我没有看过那么多中国科幻,只是我看的比你们多,不能算多;第二,一个中国作者和另外一个中国作者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中国整体和西方整体科幻作家的差距。所以,你要我回答这个问题,我确实回答不出来,我只是觉得你们以前认为中国没有好科幻,但是其实中国有很多好的科幻作家写的东西我很喜欢,然后翻译出来好像大家也都很喜欢,这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是这样回答的。但是我觉得可以更深入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想,为什么中国科幻会在西方受到这么大的欢迎?可能有人说有一部分是因为很多西方读者想对中国了解一下,因为中国现在在世界上越来越重要,他们想要了解中国,他们认为看科幻是了解中国的一种方法。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有些制度上的问题,中国科幻可能会看到其他中国文学里写不出来的东西。这种看法当然也有它的道理,但是比较狭隘,对作者和读者都是一种不尊敬。我是非常不喜欢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说为什么中国科幻给西方读者带来看不到的东西,我觉得不那么简单,我觉得《三体》、《北京折叠》是很独特的,但不能说所有的中国科幻都是它们那样子的。每个作家都很独特。不过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你们觉得中国科幻对西方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不同之处?

讲座现场
吴岩:我觉得说中国科幻能给西方带来什么的话,也就是在刘宇昆开始翻译之后才开始的,之前翻译出去的一些作品都石沉大海。九十年代我接待过一些美国人,他们觉得科幻是美国的文学,当时我还拿了些译稿,问他们能不能在美国发表,回答是说不用看,为什么呢?因为说美国人不爱外国的作品,当场回绝了。但是近些年来,美国人才知道原来有中国科幻,开始逐渐的接受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变化。另外,其实在欧洲大陆是不一样的,昨天吃饭的时候意大利的出版人还在讲,他说:“美国科幻一直在我们这儿形成一种压力,其实我们欧洲的科幻非常丰富,当我看到中国科幻以后,他发现中国科幻星空也特别精彩”。我同意宇昆说的,每个作家的差别非常不一样,简单的概括很难。
贾立元:我个人觉得中国科幻的受关注,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现在除了经济上的成长,还在科学探索上做了不少突破,并且因经费的充足,做了一些体量大、很受关注的项目,这让一些西方人产生了羡慕、好奇、紧张、担忧混杂的情绪,不知道中国人到底要做什么。比如最近就有人在《大西洋月刊》上写文章,讨论如果中国人首先和外星人接触会怎么样?其中就能感受到那种复杂的情绪。我想可能很多人担心中国人像叶文洁一样吧。不过就像宇昆说的,每个作者对未来的想法都是千差万别的,现在是个思想非常多元化的时代。
刘宇昆:对,我是希望看到中国科幻更加多元化,虽然已经很多元化了。我在编《看不见星球》这本选集时,特意给每个科幻作家都选了多于一篇的小说,这样就可以看到一个人能够写出来的不同的作品,然后每个作家和另外一个作家不一样。当然,所有的科幻作家还是有一些共同之处的,但我希望看得更远一些。事实上,绝大多数我翻译的科幻作家和我差不多,都是上过大学的高材生,但我希望将来能够看到从其他阶层来的作家写科幻,我希望看看他们对未来的想法,我是很希望中国科幻作家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越来越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就像美国一样,我们越来越从以前不被关注的视角来写这些东西,所以我希望能够看到中国也是这样。
贾立元:最后一个问题,你怎么有时间做那么多事情的?
刘宇昆:我天生不太需要睡的太多。
贾立元:这种人最讨厌,问他为什么,他说是天生的。
刘宇昆:另外,我比较喜欢做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事情,把一些我觉得乏味的事情就去掉了,这样好像一天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举个例子,我上大学时,有一次第二天是期末考试,我前一晚上准备通夜学习,因为我对这个课没有兴趣,整个学期也没有去上课,不太清楚到底考什么,所以至少有一夜我应该学习一下,至少可以考个及格。我看了15分钟书以后,觉得太乏味了,我的脑子要睡觉了,不能干这种事情,我要给自己一点奖励,我就跑到楼下找一个书店,看到《星球大战》新的三部小说买下来了,我是星战迷。我回来之后说,每学习15分钟就看一章小说,这样就更加有原力来继续学习,我就开始看,看完一章觉得好像没有吸够原力,就看了第二章。后来我就说看了两章,那看四章也差不多……我就这么看下去,结果早上八点,我没有睡觉,把书看完了,就学了15分钟,然后就跑去考试,好在还是及格了。二十年后,我被邀请写《星球大战》小说。所以,我的做法是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最后总是有一些好事会发生。
贾立元:作为在大学当老师的人,我必须得说不能提倡他这种学习方式,一个学期不上课,最后学15分钟还能考过,这种事情我们不提倡。

现场互动
同学们现场提问
提问:您作为一个曾经的程序员,您的生活实际上是什么样的状态?迄今为止您看到的科幻小说里,对这个职业到底有什么误解?
刘宇昆:谢谢。我觉得一个好的编程序的人最大的特点是特别喜欢偷懒,因为他不愿意做机器做起来更容易的事情,所以他宁愿花一天写一个程序来做一件事,所以程序员是比较懒的人,这可能是我喜欢当程序员的原因之一。如果你写科幻小说如果把这个懒性表达出来,就可以说抓到了精髓。
提问:您怎么看科幻文学和科幻作品对科学家甚至政治家的影响?
刘宇昆:我觉得科幻文学对于科学的最大影响,就是培养起人对科学的感情。因为科幻里对科学家的描述是正面的,他们是发现宇宙秘密的人,这种对宇宙秘密的感情、情怀,当然对科学研究有影响的。至于对政治家,科幻小说如果广义一点的话,确实对政治家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像全世界的政治家都用《1984》里的语言描述自己的政敌,所以这种事情是非常常见的。广义来说,科技并不光是机器、计算机或者天文望远镜这些硬件,人文方面的软件也是和科技有关系的,比如像政治。我觉得政治历史就是多人一起做决定的科技史,我的意思是说,像国会、法庭、陪审团、投票选举,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发明,也是一种技术。政治史其实就是集体决策技术的发展史:从国王、皇帝发展,到对皇权和王权有约束,到各种各样的能够代表民意的方法的出现,其实就是一个技术发展的过程,所以写科幻不光可以看科技论文,也可以看一些历史、社会学的论文,想想怎么样发展出更加有趣的集体决策的技术来。其实《三体》里很多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大刘想象在未来的危机出现时,人类怎么做集体决策。我觉得那一部分是最最有趣的。
(文中部分照片由清华大学学生会时代论坛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