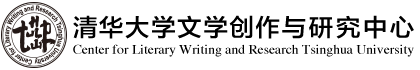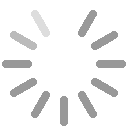世界文学研究工作坊第3讲“为变化的星球而写的文学”活动回顾
2022.05.15
5月8日上午,世界文学研究工作坊第三讲顺利举行,活动由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日新书院、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共同主办,是人文学院成立10周年院庆活动之一。哈佛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系教授Martin Puchner(马丁·普克纳)作了题为“为变化的星球而写的文学”的讲座。活动邀请了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林少阳教授担任评议嘉宾,中文系副教授熊鹰主持。线上参会人数超300人。

首先,Puchner教授提出,世界文学意味着一个大尺度的文学视角。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下所观察到的内容可能不同,而气候变化这样的主题,适合更大的时间尺度,这也是Puchner教授在其《文字的力量》(The Written World )一书中的主要观点。《文字的力量》主要涉及五个根本的问题:书写发明于何时?书写是怎样频繁地被发明?文学史具有何种形态?新书写技术如何改变故事讲述?以及口头讲故事的传统是如何与书写传统相交融的。在这五个问题中Puchner教授尤其关注第四点。如果以四千年为时间尺度来观察文学,书写系统、材料、复印方法等技术问题就成为了核心问题。
书写最早的源头之一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写于泥版的楔形文字,其发明最初不是为了狭义的文学目的而是为记录经济交易和创建国家官僚系统。最初的世界文学《吉尔伽美什史诗》就来自这个早期书写系统。用书写技术讲述故事是世界文学的第一个阶段,类似的事情也发生于其他文明,比如中国和埃及,虽然用的是各自不同的书写技术。这第一个阶段也是口头文学与书写技术的相遇的阶段。而第二个阶段是神圣文本的写作,例如宗教领域的希伯来圣经和政治领域的美国独立宣言。第三个阶段则是大师的阶段,例如佛陀、苏格拉底、孔子、耶稣,这些教师发明和传播新的思维、存在方式。这一模式有趣的地方在于,老师们总是拒绝以书写形式记载他们的言说,是他们的学生创造了新的文本。在上述书写历史中出现了两种书写技术:泥板和卷轴,而在第四个阶段,发明于中国的纸传到了阿拉伯世界,由此触发了大量故事集的产生,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一千零一夜》。随后纸又通过阿拉伯世界传到了欧洲。纸张和欧洲印刷术的结合带来了新的革命。古腾堡建立工业生产程序来印刷神圣文本,迎来了批量生产和大众文学的时代,此时大量产生的文学形式便是小说。Martin Puchner还强调,如今的技术变革时代虽然改变了我们创造文本以及传播文本的形式,这些技术革命对于书写传统的巨大影响才刚刚显露出来。但我们的技术变革的时代并非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新的发明,有时旧的书写形式会突然变得重要起来。在他向听众展示的古希腊陶罐上,一位书写者使用的写字板看起来就像是现代的笔记本电脑,新技术对于平板、滚动文本形式的偏好可追溯到早期书写时代。
其次,Puchner教授聚焦于他最新的著作Literature for a Changing Planet,围绕“如何将世界文学的视角运用于气候变化的语境”的问题展开。关于文学为什么有利于解答气候变化的问题,大多数人往往将气候变化与科学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近四十年来气候科学确实在气候变化的解释与预测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但依旧不足以解决气候问题,因为仅凭科学事实难以真正说服个人、企业以及政府去改变行为和习惯。而在这方面文学恰能大显身手。人类是爱好且擅长讲故事的动物。在故事中,人类讲述自己以及与他人和环境的关系,由此讲述世界。研究文学的专业学者可以用诊断式阅读来对气候问题有所贡献,即找出现今有关气候变化的那些故事的来源。在这方面,世界文学将特别有用,因为它与气候变化特别有关。那些故事融入了作为人类的集体想象,事实上人类有关气候变化的叙述非常的古老,它被不断地讲述,持续了几千年。因而只有通过阅读四千年的世界文学,读者才会明白为何如此难以改变人类的行为。
Puchner教授以《吉尔伽美什史诗》为例说明了解读的可能性与丰富性。其一是史诗中大洪水的故事,这也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讲述大洪水的文本。洪水是一个有关生态危机的常见符号。《吉尔伽美什史诗》和希伯来《圣经》都有关于洪水的描述。不过两者之间有不同之处。在《圣经》中,洪水是愤怒的上帝对于人类违背上帝的诫命的惩罚。这一叙述方式也体现在当代的灾难电影中,人类有罪,因而遭到惩罚。但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洪水并不具备强烈的惩罚性的道德色彩,而是古代的一种控制人口的手段。两者的区别对于今天的我们颇有启发,比如说,我们应该如何叙述生态灾难的原因,是用道德模式呢?还是用一种更类似于工程学控制的模式呢?更有趣的是史诗的主线,即吉尔伽美什与恩齐都的经历。恩齐都本来是神明为了改变吉尔伽美什而创造的生物,他与其他动物生活在森林中,直到被人类女性引诱,不得不走进隔开森林与城市的围墙,在乌鲁克学习成为人类,他开始食用加工过的食物而不再生食食物。值得注意的是,乌鲁克代表了一种最早的城市化进程,它的城墙则象征了人与动物的界线,而史诗对这座城市与城市生活大加称赞。为了推进城市的建设,吉尔伽美什和恩奇都一起斩杀了森林的守卫,尽管这只怪兽与恩奇都本是同类。在这里,史诗展现了早期的资源开采,这种榨取环境的资源开采是城市扩张的唯一路径。美索不达米亚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很远,因为大量的树木被砍伐,因而史诗主人公吉尔伽美什与恩齐都不得不远涉黎巴嫩。尽管《吉尔伽美什史诗》赞成城市化进程,它也间接揭示出了这一过程的巨大代价,指出了城市化只有通过榨取资源才能完成的定律。因而可以说《吉尔伽美什史诗》是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性文本。生态危机绝不仅仅存在于作家近四十年、甚至工业革命以来近两百年的作品中——现在的生态批评往往仅注意这些离我们较近的时期——它早在几千年的世界文学经典中就已经存在了。
除了诊断式解读以外,与生态相关的文学研究还有另外一项任务,即寻找正确叙述新故事的方式。关于故事的探寻路径有很多种,学者们往往聚焦于故事的分类,但他认为,故事中的主体(agency)更值得生态研究的关注。故事主体又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个人主体,比如说Joseph Campbell的“千面英雄”理论(A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然而由于气候问题是集体导致的问题,因此个人主体难以发挥作用,集体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新叙述中的主体。对于集体主体的叙述而言,《共产党宣言》是一个极佳示例,尤其是它叙述新的集体主体的方式。《共产党宣言》不仅是政治叙述,更是文学叙述,因为它诉诸故事的文学讲述,而且专注于创造一个新的集体主体,即无产者。
最后,他表示新的故事不仅需要集体主体,还需要集体的叙述行动(collective act of storytelling)。许多故事集都曾做到了这一点,如《一千零一夜》(Arabian Nights)、《五卷书》(Panchatantra)等。它们收集了大量的个人叙述,并以某一问题为焦点将这些叙述组织在一起。当下的世界文学研究需要做的正是以气候变化为焦点,重新整合故事叙述,并构建新的集体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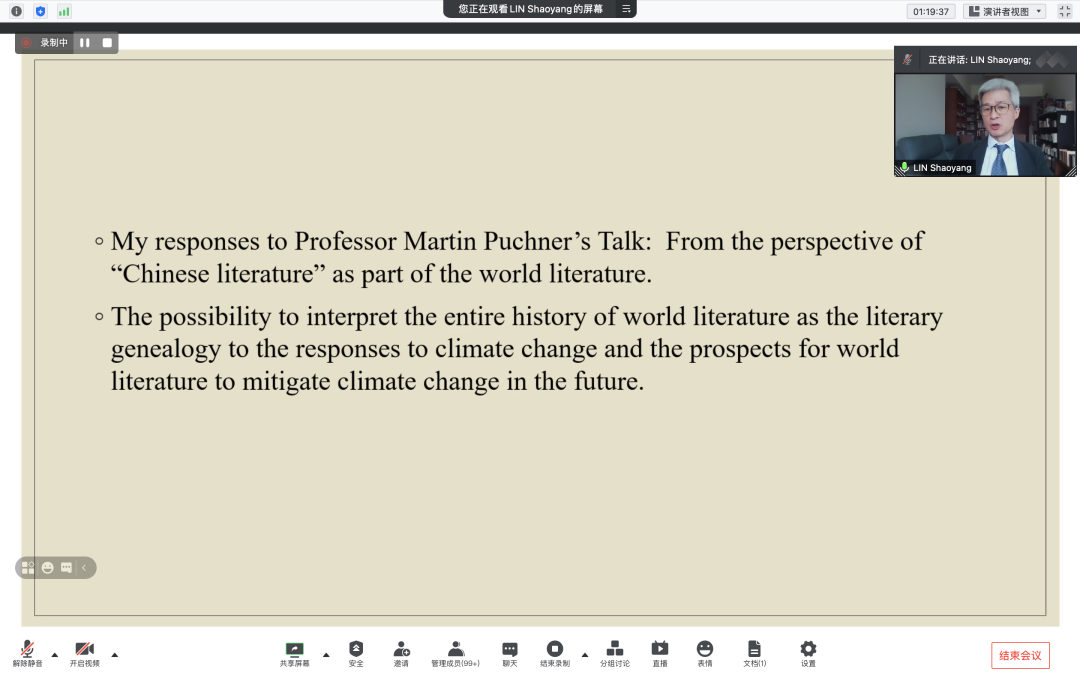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林少阳教授评议
评议环节,林少阳教授从“作为世界文学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这一角度对Martin Puchner教授的演讲进行评论,非常赞同Puchner教授将世界文学史解读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文学谱系的可能性,思考世界文学如何在缓解气候危机的问题上发挥自身作用。林少阳首先指出,现当代中国对于“文学(literature)”的理解是以“小说(novel)”的对应翻译为核心的,而Puchner教授则是从更广义的层面对文学展开讨论,包括《吉尔伽美什史诗》、《圣经》等宗教文本、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政治宣言等。而这一传统在我国的文学史中也是存在的。萧统认为文笔二分,有韵为文,但林少阳认为,萧统的这种划分是一种纯美学意义上的划分。在他看来,更为开放的关于文的定义来自章太炎。章太炎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因此,其“文学”便是其“文”之“学”。章太炎的文学概念继承了周秦汉时期的文学概念,是对基于美学和纯文学的“文”之概念的批评。在评议的第二部分,林少阳从文学对气候变化的回应这一角度出发,进一步考虑将中国“文学”重新解读为世界文学组成部分的可能性。他认为,与Puchner对古代文明特征的认识一致,中国古代文明也存在作为管理系统的文字系统和城市化这两大标志。林少阳随后对夏商周时期的文明状况、资源开采与利用、城市化进程以及气候变化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指出大禹治水传说与《吉尔伽美什史诗》及《圣经》文本中的洪水主题的相似性。林少阳以“象”和“为”的古文字为例,指出在商代人和大型哺乳动物之间是有较多互动的,人们用“人引导象”的意义,在“象”字的基础上造出了“为”字。但随后环境急剧遭到破坏,黄河泛滥。在此基础上,他引入日本学者浅野裕一在《古代中国的文明观——儒家、墨家、道家的论争》一书中针对儒、墨、道三家自然与文明观点的分析,并介绍了可以作为生态文学体裁之一的山水诗及其与山水画的特殊互动,由此阐发中国古代文学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提出将中国文学作为环境文学阅读的意义。此外,林少阳还提到《淮南子》中的“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一句,结合墨子对“鬼”的三种分类,引入浅野裕一的观点,指出鬼的哭泣揭示了鬼(The spirits or ghosts)与人类形成对立并从城市化的、书写文字的世界逃至远山。评议的最后一部分,林少阳主要讨论了如何在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学、历史整体框架下重新定义“世界文学”。他一方面以《山海经》中以山海为导轨并由各种奇异生物构成的世界为例,说明了作为世界文学组成的中国文学中的反人类中心主义框架;另一方面,他追溯自歌德以来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源流,认为Puchner从生态批评或环境阅读的角度出发,重新诠释“世界文学”,将文学和文学研究本身转变为一种环境保护的社会实践,把阅读转化为减缓气候变化的实际行动,并尝试解构现存的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民族国家文学框架,构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从而寻找文学中宏大的集体主角,即人类或人类与环境问题的关系。
互动环节,线上听众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提问。针对为何强调“物种(species)”作为新的集体代理人的作用这一问题,Puchner教授认为,在人文研究中,我们需要关注特定群体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但美国更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于特定的组织,因而把物种作为一个思考单元是一种新的开始。如果以大尺度来看人类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气候变化的确是一个物种层面的问题,而我们需要的正是一种集体的主体。被问及书写(writing)和艺术(art)的力量的区别,Martin教授指出,艺术具有其独特而强大的力量,而书写的力量的重要性在于其对故事讲述(story-telling)和城市化变革的记录,同时,书写技术的变革常常会改变文字和图像(images)之间的关系。在对人与非人的关系的认识问题上,Martin教授则结合古代和当代文学作品给出了具体的阐释。
最后,熊鹰副教授就方法论提出疑问。她认为,Martin教授的分析常常是通过情节提取来完成,但现代主义文本有时是难以提炼情节的。对此,Martin教授表示,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和将故事讲述者纳入考虑是小说分析时的重要手段,在互联网时代会诞生更多以不同方式讲述的故事,同时,他也指出,对现代主义文本的分析仍待进一步研究。
文 | 日新书院 李佳颖 李晨 朱馨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