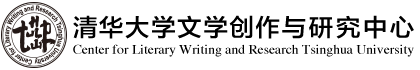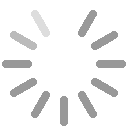朱自清文学奖获奖感言——三等奖获得者莫家楠
2018.11.24

在座老师们、同学们以及文学爱好者们,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新闻与传播学院七字班的莫家楠,我的小说《稻禾深处》获得了此次朱自清文学奖的三等奖,我感到十分荣幸。
我是在今年夏天完成这篇小说的。小说是虚构的,但它表现的人物、传达的情思、展现的风情,全都来自于我的故乡: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我在那里度过了十八年。
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来北京读书,是我第一次离开黔东南州。我是侗族人,我们那里的人种水稻,四月播种,五月插秧,九月收割,冬天在田间撒下油菜籽,春天一田田的全是金灿灿的油菜花。日子就这样在田野间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插秧后,人们就会把草鱼放入田中,任它们在秧苗间自在游动。水稻吐稻花的时候,人们就把吃饱了稻花的草鱼捉来做腌鱼。我记得小时候,我喜欢搬个小凳子看着我的父亲杀鱼,这是我童年里印象极深的一件事。
家乡人还喜欢唱歌,当地流传着一句话:“饭养身,歌养心。”唱歌对我们很重要,去年有一个村的人犯了很严重的事,搞坏了名声,县政府除了一般的责罚外,还取消了这个村三年内参加歌会的资格。
这篇小说其实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情书。里面的人物流淌着的是我家乡人的血,那个村子就是我生活的村子。红色的土地,孕育出了这样一群喜欢吃酸食、喜欢唱歌的生命。
我一直相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话。优秀的作家,都会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民族性。这种民族性,既包括中华民族这个大概念,又包括地方文化这个小概念。《巴黎圣母院》的世界和《红楼梦》的世界是不同的;哪怕是国内的文学作品,《白鹿原》表现的黄土高原风情与《草房子》中的苏北农村风情也各有各的魅力与特点。我也一直想写一篇这样的小说,也许目的性太强,导致有些情节的处理比较生硬。
最初,这个故事只是以一个场景的形式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初夏的傍晚,一轮红日被马车驮走,在天边与远山完美相切,它洒下的金光罩在炊烟袅袅的村子上方。一个小男孩儿坐在村口的田埂上看着夕阳西下,绿汪汪的水田包围着他。
后来,越来越多的素材在我脑海里积累,我的大娘、我的外婆、村里的杨木匠——我的家乡人的故事融合在一起,再包裹上侗族人特有的文化环境,最终形成这篇小说。
主人公祥子,是一个在黄土高原土生土长的孩子,因母亲改嫁而不得不来到继父所在的云贵高原生活。自然环境的不适应、对侗族文化环境的陌生以及对继父的抵触,使他与新家格格不入。
祥子,是“我”的一部分。我们村离县城不远,随着城镇化的进程,我亲眼目睹,吊脚楼被一栋栋水泥房取代,人们嘴里哼唱的从侗戏变成了流行歌曲。而许多民俗在我出生前便已消失,如文中描写的抢婚、行歌坐月,我是我这一辈人中少有的会说侗话的人。每次来到侗族文化保存得比较好的我的外婆家时,我表现出一个异乡人才有的新奇。
我和侗族文化之间,有一种割裂感。就像祥子一样,我有时会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观望着这片我从小成长的土地。我热爱着孕育我的故土,但又觉得我一直在它的周边游走,从未真正抵达它的内核。我很迷茫。乡村在振兴的同时,也洗涤掉了地方独有的文化烙印。这些烙印包裹着的东西,叫做乡愁。
侗族文化的流失不是个例。秦腔、三峡号子、花鼓戏等传统民俗,都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拥有着文科生强烈的人文情怀,我对传统文化的落寞很是敏感;看着它们一点点成为历史,我很痛心。这也是我这篇小说想表达的东西。
张嘎老所代表的就是这一类凝结着乡愁的文化烙印,他其貌不扬、让人没有亲近的欲望,但当你真正与他产生联系,你的心就会被触动。在小说的结尾,他死了。他的死去不是为了煽情,而是我想表达乡愁在城镇化的车轮下已被碾成粉末,飘散风中,无可寄托了。
近年来大热的部分小说给我一种空中楼阁的感觉,反映小人物命运或传统文化的作品少了。我希望社会在发展的同时,人们能回首观望一下那些要被我们遗忘的传统文化,希望文学工作者在创作中能念起脚下的土地。谢谢大家。
感谢莫家楠同学对本文的授权。